曾文誠回顧嘉農歷史

隨著電影的上映,最近好像有股「嘉農熱」的感覺。最早我對嘉農棒球有深刻印象的是在職棒元開幕戰前的酒會,當時王貞治先生知道三商虎球員藍文成是嘉農球員後代時,那時王先生眼中閃出的光芒是讓人很難忘的。
接著是陳潤波教練生前跟我提的事,他說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從台灣整裝往南洋出發時, 火車上的日本兵都會互相提醒「經過嘉義記得叫我」,因為他們想看看來自嘉農棒球隊的故鄉長什麼樣?
這讓我對這支在當時台灣棒球史很少被提起的球隊充滿了無比的好奇。
1992年我終於遇到了1931年嘉農棒球主力先發的蘇正生先生,當時蘇老先生雖然已高齡近八十,但仍每天從家裡騎踏車到嘉義運動,採訪那天我們約在嘉義棒球場,他也是騎車依約而來,那時的他面色紅潤、聲若洪鐘看起來就像五十出頭的「少年仔」。
採訪完蘇前輩,更讓我對嘉農這段歷史及其前後台灣棒球史的背景的想要探究的興趣,所以之後又花了幾年的時間,找了些資料陸續發表在期刊、書籍還有網路上。
現跟各位分享的是1993年發表在職棒雜誌上蘇正生先生的口述歷史,會選這一篇是因為由當事者第一人稱敘述或許更能精準地傳達某些史實。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願以此文紀念當年一起和我採訪,現在天上的聯晚記者王晶文先生。
以下就是蘇正生先生的口述:
「我怎麼會去參加甲子園大賽?說起來還是件很有趣的事。1927年我讀嘉農時,最初是網球隊的隊員,棒球碰都沒碰過,為什麼沒碰過,因為不敢。那時候棒球、日本人口中的「野球」,根本沒有幾個人敢玩,「因為聽說棒球很硬,打在身上會把人打死,會打死人的東西有誰敢去碰呢?所以棒球就只有日本人自己在玩。
「有一天我們學校老師把他兒子帶到學校來,他一個人就拿著手套在校園裡丟,不知為什麼他手上的球卻硬砸在我們同學身上,「碰」一聲!我心想糟了,可是一看沒事也就放心 了,在旁邊的我也親眼見到棒球根本不會打死人,儘管多年後知道老師兒子手中的球是軟式而非硬式棒球,不過就是從那一刻起增加了我的信心,而報名參加了棒球隊。
「嘉農棒球隊成立於大正五年,在全校五個年級當中,參加棒球隊的學生差不多有十五、六位。別看我們球隊人數少,組成的分子還擁有「三族共和」的封號,那是因為球隊內的球員是由愛好棒球的日本學生(大和民族),來自東部有棒球根基的高山族,還有參加擲遠比賽第一名被拉到棒球隊的劉蒼麟(1984年奧運國手劉秋農之父)及我這個「不怕死」的本地人(漢民族)所組合而成。
「有球員就要有教練,我覺得一支球隊的好壞教練實在很重要。嘉農能打得好,就是因為有一位好教練帶領。我們教練是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並且是該校棒球隊隊長的近藤兵太郎老師。
「近藤老師訓練我們這支三族共和棒球隊只有兩個方法、實練和苦練。什麼叫做實練,那就是每個動作都要求確實,接捕球時不管飛球或是滾地球,一定要用雙手接捕,近藤老師說用單手接球那是「花俏棒球」,一點都不實在,用雙手接捕球的好處除了確實之外,萬一第一時間無法把球接住,也能很快的撿球,避免「球漏遠了。除守備之外,打擊、跑壘,也都要求我們每一個動作要做到確實,如有一點馬虎一定被他當場斥責,直到改正為止。
「要做到技巧確實只有從苦練著手,那時候的嘉農棒球隊不像現在(1992年)的棒球隊是集體行動,而是採誰有空誰就去練的方式進行,因為唸的是農校,所以實習課程占了很重的比例,那時我們都是上午拿著鋤頭在田裡實習後沾著一身的泥,然後到現在嘉義棒球場附近的練習場報到。由於每一位隊員練習的時間都不太相同,因此近藤老師就採用彈性方式訓練,例如只有九個人在場時,就四個人打擊、五個人守備,隔段時間再交換。
「雖然時間人數不定,但絲毫不影響老師的態度,在他的監督下我們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而且不管球員是日本人或是本地人,只要穿著球服在場上都一視同仁,那只有一個字、練!
「苦練加實練之外,我記憶中近藤老師還有幾點是令人難忘的,他不淮選手在光線不足的地方看書,因為這樣會對視力造成傷害,一個視力不佳的人怎麼打好棒球呢?還有老師有一帖治感冒的「秘方」,那就是連擊三、四十個球讓他接,直到跑出一身汗「不藥而癒」為止。
「要唸書又要練球,我們卻都沒有人喊累,而且在訓練時間沒有嚴格要求下,我們不但沒有偷懶還準時到達球場,假日甚至主動練球。我們為什麼這麼做,因為我們有目標,而這個目標就是甲子園。我不知道隊中其他同學怎麼想的,但我只要想到甲子園,就會聯「想到飄洋過海、到日本到處走走的念頭,大概是這種「想玩」的心,才讓我忘掉揮汗練球的苦吧!
「在嘉農之前,代表台灣參加甲子園的,都是台北那三個學校:北一高、北高工、北高農,三個學校在輪流,所以北部人就說優勝旗不會過濁水溪。
「我進入棒球隊的第一年,參加在台北園山棒球場舉行的代表權大會,我們一路過關到最後一戰和台北一中爭冠軍,那時我是三壘手,比賽到第六局時,嘉農以一比二落後,可是後攻的我們,卻在只有一人出局進佔二、三壘,只要有一支安打就可以板平甚至超前,你可以想像那時候我們有多高興,可時老天偏偏不讓我們太得意,雨水先是一滴一滴的下來,最後像是有人在上頭用臉盆潑水一般,嘩啦、嘩啦直下,比賽就在我們準備贏球時停止不動了,等了一陣子雨還是下不停,大會就宣佈冠軍由五局結束時領先的台北一中獲得,現在想起來還是很不甘心。
「輸給老天爺不甘心的當然不只我一個人,所以第二年我們練得更勤快,加上又補強了幾位好手,雖然沒有跟其他社會組或學生練習比賽的經驗,但我們每一個隊員心裡都清楚、我們比以前更強了!
「1931年我們再度北上,記憶中那年代表權大賽的隊伍除了嘉農之外,還有北一中、北二中、北商、北工,嘉中、南一中、台中一中、雄中、中商等學校,不過最後和嘉農爭冠軍的仍是台北「三大校」之一的北商。
「我們和這所都是日本子弟的學校打完九局,兩邊都是十比十平手,延長賽的十一局上半,我們先得兩分,北商在下半局反攻得一分又佔滿壘,在兩人出局後,對方打者擊出二壘前滾地球,站在中外野的我,看到那球被擊出後,心都快跳出來了,所幸雖然緊張,但還是贏得了比賽,勝利到來那一刻我們都哭了,因為終於可以到夢想的甲子園了。
「向日本遠征的渡輪從基隆出發,不過在出發前,總督還特別召見我們,勉勵我們要為台灣爭光,奪得冠軍而回。船坐了四天多才到大阪港,雖然漫長但沒有人覺得勞累,因為這是生平第一次坐大船看海,玩都來不及怎麼還會覺得累,不過教練近藤老師還是不免在沿途一直提醒,甚至略帶斥責的口吻告訴我們:「不是到日本玩是到甲子園拿冠軍的。」
「當我們到大版港時,離開幕時間卻只剩二十分鐘,因此近藤老師顧不得省錢原則,就帶著我們搭車火速趕到甲子園比賽場地。一進了球場數萬名的觀眾就對著我們報以熱烈掌聲,這是甲子園給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永難忘懷的印象,我想現場球迷會給我們最熱烈的歡呼,除了因為我們是來自日本本土以外的隊伍,另一原因是經年苦練的嘉農球員,每個人皮膚都已呈現黑金色,讓當地球迷感覺到是支訓練有素的隊伍。
「也由於一開始就受到極大的鼓舞,因此我們都有那種強烈的意識,意識到我們一定能在此地創下佳績。另外讓我們有那種強烈贏球感的還有幾點原因:第一是開賽前看到對手練球的情況,讓我們很有信心。第二在台灣聽說甲子園球場很大,可是到了現場覺得沒有想像那麼大,和我們平常練球的地方差不多,心裡就踏實多了。第三是賽前練球時,我們有兩次獲得現場球迷的讚美聲,一次是我從中外野長傳本壘給捕手,球沒有經過轉接也沒有提前落地,就飛住捕手手套而且是好球帶的位置。其二是投手吳明捷練球,他是採用標準的高壓式投法,不但姿勢漂亮而且球速驚人,每一球投進捕手東和一的手套中,都發出「啪、啪」的有勁聲響,這使得現場看球的人都心生激賞之感。
「有信心的我們在第一場對神奈川商工以三比零獲勝,而且我在第七局還有一次盜本壘得分的紀錄。第二場我們贏更多,以十九比七大勝札幌商業,我在這場比賽不但有盜壘而且還擊出三壘安打,就因為我們連兩勝,日本各界開始注意來自台灣的嘉農棒球隊,而且在台灣有分公司的日本商社也在大阪宴請我們。
「請客那天吃的是西洋料理(西餐),第一道上的菜色是奶油麵包,以前我們根本沒有看過那一小塊黃色的奶油,不知道做什麼用的?所以大家都不敢動它,後來有一位隊友忍不住用手拿起來咬了一口,大家也就一個接一個咬了起來,所以這一頓就「有樣學樣」的吃完。不過在用餐結束前還上了一道水果,那一家餐廳的老板大概不知道我們是從台灣來的,竟然把香蕉擺在最上頭,然後蘋果放最下面,如果我們從底下拿走我們最想吃的蘋果,整盤水果一定會垮下來,所以誰也不敢動,就這麼乾瞪眼到結束。
「準決賽遭遇冠軍熱門隊伍小倉工業,但我們仍以十比二贏了他們,至此幾乎所有人都斷定這次大會冠軍非屬嘉農莫屬,因為小倉工業不久前才在練習賽中大勝中京商業,而中京商業正是我們接下來冠軍賽的對手。
「唉!世事就是這麼不如人意,一切條件都有利的嘉農,竟然以零比四敗給了中京。為什麼我們會輸,講起來令人傷心。近藤老師為了這次大會,特別請來他在早稻田的隊友擔們客座教練負責投捕暗號,這位義務教練賽前並不知道吳明捷手指已經受傷無法投變化球,可是還偏偏一直做下墜球的暗號,但球已經不聽吳明捷使喚,經常在本壘前就已經落地,在中外野的我,看到球落地捕手追球的背影,心裡直吶喊「趕快啊!趕快撿球啦!」可是有什麼用呢,吳明捷就在太聽教練指示又不敢訴苦的情況下,因過多的四壞球保送而敗北。
「我一輩子絕不會忘記頒獎典禮那一幕,看著中京興高采烈的領獎,而我們卻得忍住淚水在一旁鼓掌,世上最殘忍的事,大概就是目賭別人在你面前拿冠軍吧。
「六十幾年囉!每一年夏天!嘉農苦練,渡海遠征,甲子園激戰一幕幕都自動浮現在腦海,甚至那一年大賽回台灣,在台北遊行接受女學生獻花等甜美畫面也都清晰重現。雖然遺憾未能奪得冠軍旗,但回憶這一生已經值得了,因為、我上過甲子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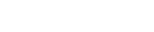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