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伴隨危險 但這股熱愛操控著生命

第二天早晨,我開始撰寫一份關於成功登頂的新聞稿,準備用無線電發送給我們遠在倫敦的遠征管理委員會。但我不時走出營帳用望遠鏡觀察著南壁,湯姆與米克此刻想必已經下到了第三營,而其他人應該已經回到了大雪溝的底部了。
記得馬丁跟我說:「克里斯,放輕鬆,攀登行動都結束了,不會有事的。「我得要等到所有人都下山了以後,才開心得起來。」
我很懷疑這是否是一個預感,我自己每當完成一次艱難的攀登後,下山途中總是十分的緊繃,直到回到堅實的平地,那股緊張的情緒才能夠平復下來。
我剛回到打字機前正要開始工作時,突然聽到有人狂奔疾呼:「克里斯、克里斯!」後面的話卻聽不見了。我衝出去看到麥克坐在草地上,用雙手把頭抱在膝蓋中間,大聲的啜泣著。他把頭往上抬起,整張臉因驚嚇而扭曲,悲傷而消耗殆
盡了。
「是伊安,伊安死了,他在第二營前面被雪崩壓死了!」
大夥都從營帳裡衝了出來,呆若木雞的站在草坪上聽著這個噩耗,聽著麥克哭泣著訴說這個意外的過程,那五分鐘之間整個世界像是靜止不動,寂然無聲了。
麥克是我所認識的朋友中最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中庸而和諧的人了,但這一天早晨他忍不住那恐怖的悲傷而哭泣了。在我攬著他的肩膀,試著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時,我的淚水也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麥克、伊安與大衛三個人那天早上決定不等米克與湯姆下到第三營,就提早出發了,把所有的裝備器材儘可能的扛下山來。我們也安排好讓雪巴挑夫上到現在已經撤空的第二營的營地接應他們。
麥克與伊安在早上約九點三十分抵達了第二營,雪巴還沒到,他們就決定繼續前進。伊安提議稍停下來休息吃點東西,但麥克急著想下山,因此說走快點,再半個小時就到第一營了。
他們就繼續前進下到了冰河邊緣,進入了由一些冰塔構成的窄巷中,然後行經那一列冰崖下方的斜坡。我們一向認為這個位置很危險,但是在遠征早期時,那一片被稱為「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最明顯的危險已經倒塌了,雖然上方還有其他的冰塔也有潛在的危險,但似乎不會這麼剛好在我們經過的那幾秒中突然崩塌來。儘管如此,每當經過這個危險區域時,我們仍然是加快腳步通過。
伊安一馬當先,麥克跟在後頭,大衛落在五分鐘外的距離,他們正從狹窄的巷道中走出來,正要走下那一段斜坡時,前面已經看到五位上來接應的雪巴,正在冰壁前面的一塊小丘上休息。
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一聲霹靂震天嘎響,只見一大片遮住整個天空、黑鴉鴉的龐然巨物垮了下來,麥克躲在冰壁下方的凹槽裡,他覺得在他前方的伊安好像往下坡的方向奔跑,試圖躲過這一片崩塌的冰塔,但他卻無法逃過這個意外。
「 整片天地都是黑的,」麥克後來跟我說:「我想我慘了,就躺在那裡用我最尖銳的嗓門咒罵著,這種死法真是笨呆了!」
這陣崩塌似乎持續了好幾分鐘,而實際的時間或許並沒有那麼的長。麥克在冰壁旁被一些較小的冰塊掩埋住了,因此躲過了一劫。
雪崩雲慢慢的塵埃落定後,那恐怖的、轟隆尖銳的煞車聲逐漸消逝遠去,又回到了冰河慣有的寂靜。這時,生還者從冰堆中爬了出來,雪巴們為了求生,當時也是拔腿就跑,很幸運崩塌的距離沒那麼遠,因此也避開了這個危險。明瑪還是被一個冰塊擊中,但很幸運沒有受傷。
他們隨即展開搜索,在崩塌遺跡的山腳下找到了伊安的身體從冰塊中突了出來,當時他想必是馬上就喪生了。意外發生在早上十點,麥克馬上就衝下山來,而大衛與雪巴們則留在現場處理遺體。他們隨身攜帶了無線電機,因此麥克請大衛開機待命。
回到基地營剛過中午,我打開話機,大衛在線上,他說已經將伊安的遺體從冰塊堆裡挖掘出來了。
我馬上決定要先將伊安的遺體運下基地營來,然後在這裡埋葬他。第一營所在的島丘那裡太凄涼了,我覺得我們得要有一個儀式來向這位我們最好的朋友道別。此刻我們仍然因為這個恐怖的意外震驚不語。這種感覺很奇怪,假設這個意外發生在攀登的過程中,或許還比較容易去面對,但此刻,所有的攀登活動都告一段落,我們也成功的達到目標了,卻發生了這個意外。
我不禁覺得那是我的罪過,如果不是我決定將所有的隊員都撤下來的話,或許就不會碰上這個意外。從理智上來說,我可以丟開這個念頭,畢竟在遠征過程中冰塔隨時都有可能會塌下來,在阿爾卑斯山脈這也是登山者習以為常的風險。假如冰塔早一分鐘塌下來,伊安可能就逃過了這個意外,但如果晚個兩分鐘,那麥克跟五名雪巴就遭殃了。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和接受的風險,在喜馬拉雅遠征中,你一定得接受這種風險的存在。然而,儘管你明白有這個危險,但是當它一旦發生,你還是很難去理解接受已經發生了的悲劇。
但是危機還沒有解除,米克和湯姆還在山上,現在可能已經通過第三營了,我們還要設法將伊安的遺體運過島丘下方危機四伏的冰河裂隙區。我沒辦法自己在這裡等候著我的隊員下來,因此我請尼克跟我一起上去,去接應運送遺體的隊伍,以及迎接米克與湯姆下山。
他們正要橫渡冰河的時候,我們碰面了,我很難接受這個眼前的這個景象,一付擔架用雨布裹著一個了無生氣的冰冷屍體,前一個小時他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哪!帕桑嚴肅的指揮著由雪巴與廓爾喀組成的擔架隊伍,通過這亂葬崗般的冰河裂隙,你不禁會留意到上方那張著血盆大口、蠢蠢欲動的冰崖。此時,米克與大衛也跟上來了,但是湯姆還在後頭。他們請一位倫敦雪巴羅伯在後頭接應湯姆,但是我覺得我必須上去島丘,以確定湯姆已經安然無恙的下山了。我在迷霧中慢慢的往上走,混雜著痛苦與恐懼的心情,還是沒看到人影,該不會又發生什麼事了吧?快走到第一營時,我聽到了下方一陣落石滾動的聲音,原來在雲霧中我們錯身而過了。因此我們就一起下山往回走,至少現在所有的隊員都下山了。
那天晚上每一個人都很壓抑而寧靜,每一個人都將自己埋藏在這個悲劇的思緒裡。第二天早晨,五月三十日,從波卡拉出發的挑夫預計今天上到基地營,將所有的裝備器材運下山,我們在基地營上方一百英尺處的一塊斜板岩的底部埋葬了伊安,這兒是伊安花了許多時間教導攝影隊員、挑夫以及廚房小弟練習猶瑪攀登與繩索下降的地方。我講了一些懷念伊安的話,湯姆帶著大家做了一個禱告,然後我們就將伊安埋葬在墳墓中。整個葬禮簡短而隆重,特別是這些生死與共的好友們都獻上了深深的祝福。
雪巴們製作了一個木頭的十字架,挑夫們用草坡上美麗的花朵編成了一個花圈,把它懸掛在十字架上。營帳都已經撤除了,挑夫們等候著他們的重擔,過去兩個月在此所有的奮鬥、劇情與歡笑,最後留下來的只是一堆空罐子,以及一個孤寂的墳墓,裡面躺著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與安娜普納南壁道別,轉身下山,這是過去十個星期以來第一次回到基地營下方的冰河。上來的時候所有的景物都深埋在雪堆之中,但如今碎石堆露出了它的身軀,一道滿布灰塵的小徑穿梭其間,它讓我覺得好像是一個廢棄場一般。越過了冰河來到對岸,往下穿越了末端冰河側邊的峽谷,四處都是青翠的草原,點綴著各式各樣的野花。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對於遠離了安娜普納南壁,朝下直直切入了深邃的莫迪峽谷一點也不會感覺遺憾,我們在山上待得實在太久了,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也都明白這是我們登山生涯中最精采的一次遠征,我們共同團結努力,終於成功登頂。自莫迪河谷漫步而下時,我們的心情混雜著悲傷,因為一位好友過世了,以及格外的興奮,這不只是因為成功登頂而高興,是因為我們成為了一個緊緊契合的團隊。
我不敢去思量,相對於一位好友的生命,以及我們所投入的青春與花費的金錢所得到的這個成功,到底是否值得呢?登山以及所伴隨的所有危險,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對絕大部分的遠征隊員而言也是如此,那自然也是伊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當你結婚成家後,登山的危險很難被認為是值得的,我想我們大部分的朋友已經不敢再去思索這個難題。我們就是愛登山,這股熱情操控著我們的生命,引領著我們來到安娜普納的聖殿。
莫里斯.赫佐格在他描述安娜普納峰首登的故事裡,用了一句話做為他的結語:「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自己的安娜普納。」誠哉斯言,無論是在登山探險的世界裡,或是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上,皆是如此。安娜普納峰南壁的登頂,象徵著喜馬拉雅巨峰大岩壁攀登時代的開端,而不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登山者會嘗試去尋找其他更為誘人的目標,或許會以更少的人數來攀登這些龐大的山壁,並揚棄這種極地遠征的方法,採用阿爾卑斯式的快捷方式來挑戰這些巨大的難題。
我們每一個隊員,也都會找到自己新的目標,唐與道格爾將嘗試挑戰聖母峰西南壁,湯姆繼續探索虔誠信仰的摩門教徒生活,米克則會嘗試開拓他的攝影事業,而我呢?此刻還不清楚,我相信我的生命中會有更多的安娜普納,每當達成一個目標後,自然會再去尋找下一個安娜普納。

本文選自 臉譜出版《靈魂的征途》一書。
位於喜馬拉雅的安娜普納峰是世界第十高峰,而「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自己的安娜普納。」到底危險的海拔,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挑戰?
人們需要山,因為登上山頂可以眺望整個景觀,整座城市彷彿被渺小的自己看透一圈,心裡的迷惘也黯淡一些,或是登山過程中的挑戰就是生命裡追求的熱愛。山能夠創造身體與心靈之間的對話。
本書帶領讀者離開地面,由20世紀重要的登山家—鮑寧頓親自撰寫,描述一批登山者如何在極端的環境考驗下,準備裝備、搬運糧食、擬定戰術,以及臨場反應到如何掌握人心,從中使出渾身解數並險中求勝。
◎書籍資訊:https://pse.is/3hmkmh
◎ 更多戶外資訊請見: 山林野趣粉絲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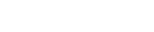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