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一天來臨前-鈴木一朗

文/陳彥儒
前言
或許這正是運動員的宿命,亦是平凡肉身軀殼不可免俗、所逃不過的休止符…
有人說:運動員一生得面臨兩次死亡,一次是生命的自然殞身、一次則是步下舞台之時。
曾經,我們以為這名名喚為「神」的男人可以抵禦這種不可逆。
直到歲月逐漸侵蝕他的肌腱,臉上皺紋無情印刻於其面容,我們才發現原來鈴木一朗終究也只是人…
而時間終究追得上跑得再快的任何「人」…
五月突如其來暫別球場的訊息,容或預示著最後的離別即將到來,在一朗正式道別以前,我們還有機會再次見到那象徵日本最美麗、最純粹、唯美而詩意的揮擊嗎?
如櫻綻放、如櫻紛落
「鈴木一朗是位以棒球場為畫布的藝術家。」──《紐約時報》
在所有棒球迷記憶中,當鈴木一朗站上打擊區時,那是一種無聲的岑寂;在片刻寧靜裡頭,那臂上指南針隊徽亦特別閃亮,彷彿就像是在指引著球迷雙眸所該定睛凝神之處;接著,我們看見他輕撩衣袖,舉起殺敵利器逼視敵手,並以世間絕無僅有的從容、毫不霸道、優雅的完成那輕盈、簡潔堪比日本白雪的揮棒;在鎂光燈下,那已是棒球場上可以捕抓到的最美視覺印象。
「美產生自對象,而崇高則萌生於主體心靈,比起美來說,崇高更為主觀,美感有時僅是單純的快感,而崇高則是由壓抑轉到振奮,故觀者心靈處在動盪狀態。」這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談到美、乃至於在向上昇華的見解;而這正巧也可用以詮釋一朗,換句話說,不單是形式上的華美,當資本主義迅即萎靡社會的主體精神時,他以一種形而上的追求,喚醒了每個人心底對於靈魂的共鳴;可以這麼說,在一朗身上,我們幾乎看見了所有日本的崇高象徵。
光是欣賞一朗打擊,我們就已然覺察到一種近乎無可挑剔的完美,有人說,棒球是種機率運動,但他卻像是破壞這項法則的男人,能在不到一秒的快速反應內,宛如雕工細琢、對任一尺寸間距都能切割的生魚片師傅,將球兒俐落的以純熟刀法、不偏不倚劃向球場任一空曠處。這種細緻之美讓他曾經在日本職棒創下連續216打席無三振的誇張紀錄、甚至在太平洋彼岸留下屬於自己的安打傳說,呼應「日式職人」對於各項細節的至高苛求。
當一朗站在鑽石綠野時,我們則看見靈動如忍者的曼妙姿態,壘包間,他被稱作「3秒8的男子(據傳這是一朗從本壘到一壘的速度)」,對於他來說盜壘如拾草芥,輕易在日美留下千盜神話;2012年10月8日,那是一朗披上條紋戰袍後所面對的第二場季後賽,當時他繞過三個壘包直闖本壘,眼看即將成為生涯罕見的錯誤跑壘,在這必死攻防中,儼如忍術密技瞬身術,其以泥鰍式的閃身動作成功迴避觸殺幫助洋基拿下關鍵分;而後,「忍者一朗(Ichiro ninja)」就成了其中一個屬於他的Google 關鍵字。
還有什麼野球上的技藝難得他?即使是拿著手套,依然令人望而生畏;沒有變種蜘蛛咬傷,他卻仍能輕易用攀牆方式沒收一支又一支的全壘打,那雙矯健的雙腿早已達到奔跑跳躍如履平地的境界;當立場互異時,一朗則化身狩獵場上最精準的狙擊手,用那迥異於亞洲「弱肩」的強大臂膀、傳出一次次不落地的雷射獵殺;相較美國大隻佬們的暴力美學,身高不足180的一朗在防守上似乎更值得被稱之為藝術品。
之所以能夠如此將心、技、體這般完美調和,背後所代表的即是那涉及到形式之外最崇高的精神發揮;你可以很簡單就從一朗身上找到所有日本遺失的美好傳統;當2001年越洋踏上美利堅沃土後,他僅用手中那支細薄長33.5英吋的楓木棒就詮釋所有東方文化該有的內容涵養;更難得的是,一朗並不封閉,為了融入美式球風,他願意改變揮擊方式(原本是鐘擺式打法),調配出美日合併的獨一風格;如果說是武士,大概就像接受西方洗禮的坂本龍馬一樣,走在時代的前端,用嶄新的方式讓所有觀球者都能在3小時的振盪中認識何謂武士道。
數十年如一日,每年近162次,從日本國花櫻花綻放、春訓伊始那一刻,我們跟隨節氣欣賞這曾以為會亙古恆常的美好;然而,正有如櫻花的表徵:在極短花期中努力地綻放,並在最為絢爛的時候、繁華落盡;無巧不巧,也就在今年五月櫻花季結束時,夜未眠的西雅圖傳來大家最不想聽到的消息:「鈴木一朗將暫別球場,從球員轉為總經理特助。」
縱然我們明白所有壯麗淒美的詩篇都不該冗長,但帶有意猶未盡的句點,還是讓人既錯愕、又失落;儘管一朗未曾說出「退休」兩個字,但大家瞭然於心的是,球員終曲的輓歌奏起,距離運動員第一次死亡的那天已不遠矣,我們還有機會再次見到那象徵日本最美麗、最純粹、唯美而詩意的揮擊嗎?
【完整內文刊登於美國職棒雜誌2018年 六月號】
https://www.facebook.com/mlbmag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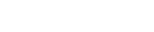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