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盯著的登山者們:登山政治學

©BERNADETTE MCDONALD 2011|繁體中文版 © 臉譜出版 2021
登山政治學Climbing Politics
此刻,重點是將生命賦予萬物。讓疑問鮮活起來。也許,之後,在遙遠未來
的某一天,慢慢的,甚至連你都沒察覺,你就開闢了通往答案的道路。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給青年詩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
在波蘭,做一個登山家絕非易事;儘管這國家總愛吹噓它多采多姿的悠久登山歷史。早在一九二四年,波蘭的登山家就在策畫攀登聖母峰1與K2峰。這時,這國家還在舔舐與布爾什維克蘇俄血戰後的傷口。愛國情緒高漲,一九三○年代,波蘭人建立專屬的山岳俱樂部。即便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俱樂部依舊勉力運作。一九四九年史達林政治系統接管,情況為之大變。蘇聯倒沒有全面否定登山,只是改弦更張,認定登山是一種個人經驗,含有「小資產階級逍遙山岳的餘毒」,於是轉交宣傳機器壟斷,操作為集體奮鬥的成果。定位調整最直接的衝擊就是限制攀登塔特拉山脈。登山者被迫躲避邊界巡邏員,或者提出研究調查申請。這種策略不大容易成功。波蘭人天生反骨,只要逮到機會,就一定會擅闖禁地。
赫魯雪夫與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2主政,政治氣氛略略鬆弛,鼓勵山岳俱樂部進行改革,但限令依舊繁複。鐵幕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對外打開一條門縫,登山家立刻蜂擁往西─挺進阿爾卑斯山。他們渴望趕上西歐同好的登山技巧,儘管資金嚴重不足,但他們還是席捲阿爾卑斯山周遭,克服諸多艱險,攀登好幾座難以跨越的高山,讓人眼睛一亮。一九六○年代初期,他們盯上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山勢參天、容易接近、費用低廉,集諸般好處於一身。隨著波蘭真正民主化的期盼落空,登山家放棄在祖國發揮潛能,開始朝國界外眺望,試圖規避日復一日的煩悶與單調。
諷刺的是:讓他們悶到幾乎窒息的政權,竟然提供他們奔向自由的門票。中央政府很樂意批准他們去海外登山,在國際揚名立萬,光彩收歸祖國波蘭。
當時登山界的主流思維建立在全面性的古典模式上:不只登山技巧,對於登山歷史、文學、藝術與傳統,也要能全面掌握。孕育與時俱進的登山文化,精神搖籃並不在華沙的山岳俱樂部辦公室,而是在塔特拉山脈「海洋之眼」(Morskie Oko)3周邊的小木屋。在白日漫長征程後的燭光之夜,口述傳統萌芽滋長。這是一個充滿故事、歌唱、夢想與激烈辯論的地方。這是一個登山家感受到自由的地方。
出征海外的登山家固然感受到掙脫藩籬的喜悅與暢快,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非成功不可的壓力。在這種心態下,登山家扎實的訓練、絕不放棄的堅持、在極端環境下幾近自虐的抗壓力以及強烈的浪漫英雄色彩,諸多因素相互激勵,造就了豐碩的成果。
登山已然演進成為一種休閒活動,各個階層都可以來嘗試一下。不久之前,登山家還自認是波蘭社會中的一種次文化。二十世紀前半,被視為波蘭登山界的靈魂首腦、山岳作家史沙潘斯基(Jan Afred Szczepański)曾經寫道:「登山並不是人生的象徵或者詩意上的隱喻─登山就是人生本體。」
關於登山家的流言四竄。登山家的生活很舒坦,到國外旅行冒險,還可以暗地裡搞些買賣,狀似有利可圖,吸引越來越多人加入山岳俱樂部。諸多俱樂部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整併成為波蘭山岳協會,卻因此引進更多的官僚習氣、繁文縟節。每個登山者都給發放一張官方卡,標明此人能在何時、何地登山,幾乎等於執照。在一九七九年前,在波蘭,活躍的登山者共計兩千四百人。俱樂部倍數激增,大學社團也來湊熱鬧,自立門戶,成立專屬組織,想以大學生的「運動項目」為名義,搶食中央政府預算。
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一九七○年代創設的「青年社會行動基金」(Fund for the SocialAction for Youth,FASM)。基金成立的目的是讓年輕人有機會,以較低的稅率多攢點零用錢,去買家具等必需品。為了保持某種控制,就得在官方認定的俱樂部打工,才能有享受較低的所得稅率。波蘭山岳協會(以往的登山俱樂部,現在都改成這個名字)只要公開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組織」,就被視為合法打工的俱樂部。登山者將他們微薄的收入存起來─不是為了家具,而是出國遠征!
俱樂部成為這個國家中的微型社區。人們不只在俱樂部裡工作,也是為俱樂部工作。他們把閒暇的時間用來跟俱樂部裡有相同興趣、類似見解的人廝混;不關心怠惰失靈的環境,放棄職場生涯的任何期待。他們將尚未實現的夢想與飽受壓抑的能量,釋放在對於山岳的熱愛與冒險的期待上。山岳成為他們的庇護所,讓他們逃避日常生活,實現自我,創造有意義的人生。在山上,歐威爾式(Orwellian)的監視不再管用;可以回復極權政權建立前的原則─所有登山家共享的價值觀。越成功的登山家,越善於內省,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表達方式。
幾年之內,波蘭就成為喜馬拉雅登山界的霸權,當局愛死了這種尊榮感。政府宣傳機器利用登山家的成就;有成就的登山家也學會利用宣傳機器。最頂尖的的登山家得到獎章、獎牌。成千上百的人只想揮灑難得的自由,在世界屋脊上,隨意流浪。
但是登山界卻得面對越來越尖銳的道德兩難。絕大多數的登山家都反對政府,一九八○年代初期,多半還加入相當活躍的團結工聯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試圖將民主制度引進波蘭。同時,他們又深受中央支持的誘惑,被迫加入俱樂部,公開宣稱他們是社會主義者。當局密切注意他們,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吸收他們兼任間諜。有的人接受了。弗次瓦夫登山家亞列克.利沃夫(Alex Lwow)素來直言不諱,他形容這種行為是「表面順從官方宣傳的基調,骨子裡,只是想汲取當局的資源,從政權手裡拿好處」。安德烈.扎瓦達深諳世故,為這種策略辯護,宣稱西方登山家也有合作伙伴,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還把贊助者的商標縫在衣服上。當時的波蘭登山界始終瀰漫一種集體的罪惡感,好多登山家指責這種行徑是「沾上」極權國家的「糞土」。
儘管有這種道德上的角力,攤在波蘭登山家面前的選擇其實很簡單:要麼,接受政府資助;要麼,乾脆別爬山。他們選擇了爬山。他們爬得越多、表現得越好,登山運動就越讓人感到敬畏。

本文選自 臉譜出版《 攀向自由》一書。
波蘭的登山風潮在二〇、三〇年代就出現;後來二戰結束,共產政府從五〇年代中期開始鼓勵登山文化,希望藉由登山家在國際揚名,為祖國爭取光采與名聲。登山家們為了追尋自由,選擇與政權共生共存;但經濟蕭條使得登山設備幾乎無從購得,於是他們透過各種手工、從事苦力換取設備及登山的金援。本書紀錄波蘭登山的黃金年代;從攀登看見整個時代對自由的渴望、人性的堅韌,以及淵遠流長的哲學思想。
◎書籍資訊:https://pse.is/3aaaw8
◎延伸閱讀:柏林馬拉松回顧:因為我來跑了,已經和以往的人生不一樣了
◎ 更多運動資訊請見:慢跑俱樂部粉絲專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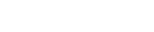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