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絲打」:企最前排持盾擋子彈、只係希望自己有啲用 冀明年考入「暴大」
「就算唔係示威者,as a 人,強身健體都係一件好應該嘅事,何況你畀狗追嘅時候,真係更加知道『書到用時鍾樹根』」Mary(化名)認真地說。「書到用時鍾樹根」是幾年前網民嘲諷民建聯前立法會議員鍾樹根的用語,形容鍾年少時唔讀書、語文能力差,Mary借用解釋體能亦如是,平日不鍛練、真要跑起來就GG(完蛋)。
「連登絲打」Mary讀傳統名校,是某政府高官的師妹。現年18歲的她是應屆文憑試(DSE)考生,但在剛過去的暑假忙於在前線擋子彈、「食催淚彈放題」。雖然暑假至今仍每星期去補習4堂,「如果要取捨嘅時候,咁就梗係捨補習(上前線)啦,我都有盡量去維持我學業有限度嘅服務,但好明顯就維持唔到,就好似港鐵一樣。」她說,希望明年可以考上「暴大政政」(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
「如果無呢個運動,我暑假應該就係:盡量打少啲機、開始溫書、補吓習,想pick up番自己嘅學業。我一路都想嘅,即係好似我想發達、我想減肥,全部都係想。你知唔知道呢個世界最遙遠嘅距離就係想同埋做,然後我一路只係想,只有呢個社運,我先至真係做。」
九月份,暑假結束,反送中運動未了,多間大專院校及中學在開學日罷課。就讀傳統名校的中六生Mary亦在校內參與罷課,接著的日子,她忙於幫手宣傳罷課、人鏈活動,周末繼續上前線。九月某個星期一,與Mary約在港島一個公園做訪問。她家在不遠處,放學回家休息一下再「踢拖」出來。訪問剛開始,她比較像是準備充足的考生,但漸漸地就流露出「絲打」氣息,過不了多久,她直接表示自己「連登味濃」。
Mary參與校內罷課,政見深藍的母親極力反對,不願意為她簽署家長同意書。Mary說:「佢好驚無咗啲個人利益,instead of 擔心我點解要咁樣做。佢完全唔care我點解要咁樣做、背後嘅理念同原因,佢只係覺得我咁樣做會影響到佢、話我咁樣做好自私。所以9月2號之後我同佢完全徹底割咗席。我而家繼續住喺佢間屋度,但都只係因為我無錢搬出去住。」
在Mary幾歲的時候,父母親離異。成長於單親環境,Mary與母親關係算不上親密,她甚至形容是「河水不犯井水」。至於父親,Mary認為他對政治不甚了解,只會人云亦云,但十分支持她,「因為我係佢嗰女,佢以我為最重要,但同佢嘅政治立場無關係。佢唔知道我係前線,佢以為我只係搞吓罷課。」Mary續說,父親最後替她簽了同意書,不料母親違反諾言,本來表示不會干預她父親的決定,後來竟打電話給她父親,叫他到學校「撤回」同意書。Mary說到這裡非常憤怒,「即係(母親)對住林鄭呢,又唔叫佢撤回,但就想叫我老豆撤回簽名!」
Mary於是找父親食早餐,解釋罷課的原因,成功說服他別撤回。Mary稱,自小由傭人照顧,認為父母「只有提供起居飲食,無任何價值觀嘅栽培,或者個人品德嘅培養」。父母亦不催谷她讀書,入讀名校只是因為小學升中一條龍。她又指,雖然有兄弟姊妹,但哥哥年紀大許多,已出國多年;細妹則太年幼,沒甚話題,所以Mary更傾向形容自己是獨生女。
「屋企唔算好有錢,但有樓留俾我,而家割咗席,冇啦。有車,但唔係用嚟車我。即係夠我衣食無憂,稱唔上好奢侈,可以一年去1至3次旅行。」成長於優渥的環境,住在灣仔私樓,13歲以前的Mary仍不知政治為何物。
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成為她的政治啟蒙,「嗰陣13歲都好難關心啲咩政治,不過叫做知道有反國教、年頭台灣有太陽花(學運)。嗰陣我都係只係知道要爭取真普選同埋點解要爭取,例如因為小圈子選舉咁。主要觸發點係928見到啲狗射Tear gas,點會諗到五年後Tear gas係最低消費。同埋自己都成日玩Facebook、 IG嗰啲,接收到嘅資訊都比較多,所以唔會話好離地。」她還記得,9月28日那個黃昏她與母親在板長食飯,睇新聞見到催淚彈在人群中爆開,遂決定要站出來。9月29日,學校停課,Mary於是一大早去到金鐘,首次參與社會運動。
那時候,同學們大多未有意識參與社運、只是影相打卡,Mary自己也不過是在街頭度過了一些日子,但她開始體會到「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那一場運動,亦促使了她在高中選修中史科,「我唔係因為讀中史所以反共,係因為我反共所以先讀中史,因為我想同人理論嗰陣可以用史例撻人,當然啦讀完中史更加覺得自己反得無錯。屌你老母共產黨殺自己人,仲多過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殺中國人。我未變態到支持日本侵華,但講真殺中國人呢方面,共產黨實在不遺餘力。」另一選修科是經濟科,「無乜好講。」
回到今天的反送中運動,Mary說:「我學校其實港豬比較多,好多都好離地,同埋有錢人都唔少,加上就算係黃,啲人都好撚乖,唔敢反抗,唔敢搞事,只會心入面支持。我都幾肯定如果今次我冇帶頭,學校一定唔會有人敢搞我做嘅嘢,不過今次運動都喚醒咗好多人,當然啦,要裝睡嘅人叫不醒,但嗰啲人就準備burn with us啦柒頭。」Mary指,校內只有相熟同學和老師知道她參與運動,但不知她走得這麼前。有已經離校的老師都很關心Mary,間中問她是否安全、為她祈禱等,她說:「feeling blessed」。
當初反對修例,她說不是因為誰人會被「送中」,而是認為「當政府得到呢個權力既時候,自然會造成嚴重既自我審查,社會進入白色恐怖,全民不敢反抗,政府更加霸道無理......去到之後,政府完全唔回應、越嚟越多問題浮面,例如黑警濫捕,司法制度嘅根本問題就慢慢浮面,跟住我就覺得呢個問題已經返唔到轉頭。」
在過去三個多月,Mary有時拿著木製盾牌走到最前排,對面就是隨時擎槍的警員,「其實係驚嘅,即係個感覺好似有人攞支槍瞄住你咁樣。」她又深覺警察有意瞄頭開槍,所以計劃升級頭盔,「而家係職安真漢子(地盤工人)嗰啲,我諗住遲啲就會升級做單車頭盔,無咁柒啦,即係你戴住個黃色頭盔,驚死人唔知嗰度係你個頭咁,所以我諗住遲啲換黑色嗰啲頭盔。」
若問為何走到咁前,她只道:「我覺得我可以勇武,咁我咪做。因為我有啲friend真係好驚,如果比起佢哋,我少咗呢份恐懼,咁我咪幫佢哋做埋佢哋唔敢做嘅嘢。」談到底線,Mary說不會揸刀/棍主動攻擊人,但有準備做「魔法師」(投擲汽油彈之類)。面對刑責,她沒有太多想像,但最擔心的不是坐監,而是在獄中遭受不人道待遇。
「其實無人想被人拉,只不過你覺得呢個地方值唔值得你去押上你嘅前途、你未來十幾年嘅青春,你都要去做?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如果佢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唔值得佢去獻身嘅話,就算佢有無膽都唔會咁做。」她說。
Mary自言身手不敏捷,但希望自己「有啲用」,所以選擇站在前排的位置。「我其中一個friend比較嬌小玲瓏,跑得勁快嗰啲,佢就做熄煙(彈淚彈),因為佢反應同身手都快,即係佢會做比較hit and run嘅嘢,我就無計,hit完run唔到,被人hit返轉頭就有份。」Mary多數都會及早起跑,「見到佢哋向前衝咁梗係走。我係拔腿就跑,跑到無雷公咁遠,跑到安全先至停嘅。但三個月以嚟都無瘦到。」
她續道:「我覺得真係每個香港人都要練吓體能,要強心健肺。就算唔係示威者,as a 人,強身健體都係一件好應該嘅事,何況你畀狗追嘅時候,真係更加知道『書到用時鍾樹根』。」
Mary認同,因為名校生的身份更容易取得媒體曝光,但她指出這身份與走上前線沒有關係,「其實名校生都只係一個外人點睇我嘅身份,唔會影響到我嘅價值,都唔會影響我喺呢個運動前線嘅位置 。我都唔會因為自己名校生覺得自己前途無可限量、大個會飛黃騰達,因而放棄一啲我覺得係正確嘅事。而且香港搞到咁樣,飽讀聖賢書,雖然我冇,更加有責任盡自己所能去貢獻呢個社會。每個人係呢場運動都有自己嘅位置,冇話前線特別高尚,最緊要搵到自己嘅定位,各司其職。」
運動已經歷時超過三個月,Mary稱母親一毫子都無俾過自己,自己也不願意問她攞錢,而且自9月初割席後已經沒有跟對方講過一句話。以往每次問母親攞零用錢,都有500或1000元,現在幸得父親和男朋友都樂意給予財政支援,她才應付到補習費、學校雜費和生活開支,「我個銀包空咗好耐,所以一打開個銀包,你想買咩都即刻收皮。」而且示威現場有人派食物,Mary說食過飯團、麻醬烏冬、咖喱飯等,說起來她都覺得自己食得太多。
開學之後,Mary繼續在周末參與抗爭活動,「暫時都仲係早放,我平時放學都可以返屋企瞓覺,但係之後,可能會慢慢適當地減少我參與嘅程度,因為我要溫書,唔好講我攰唔攰呢啲廢話,有邊個香港人唔攰。我要溫書,我真係想讀大學。」她說自己的成績屬中上游,想考上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則仍須努力。
Mary又認真說,「我覺得如果呢個運動輸咗嘅話,我係會自殺。因為你幻想到如果輸咗呢個運動,到底香港會變成點,你已經預示到好似新疆咁樣,即係你見到啲人喺集中營、畀人啪懵仔針。我接受唔到,我曾經最愛嘅香港會變成一個咁樣嘅地方,我接受唔到我要面對咁樣嘅情況。」
「希望大家吉人天相。如果呢場運動輸咗,香港死硬,好似六四咁樣,但個倒退唔只30年。我哋可以一齊去新疆,起碼一定極大規模清算所有參與過呢場運動嘅人。所以,『香港人』下一句唔應該係『加油』,應該係『退無可退』」Mary在訪問最後如是說。
觀看原文: 按此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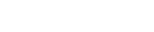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