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森林裡

我也愛過一個人。愛情恪盡職守: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她是一個溫和的白皮膚女孩,住在朗德省(Landes)的森林裡。傍晚,我們在林蔭道散步。一百五十年前栽種的松樹已經占領了沼澤,在沙丘後方欣欣向榮,發散著辛辣又溫暖的味道:世界流的汗。一條條小徑是輸送帶,我們在上面平穩靈活地前進。「必須以蘇族(Sioux)的方式生活。」她說。我們撞見一頭頭動物,一隻鳥,一頭狍子。一條蛇溜走了。古代(Antiquité)的人──大理石的肌肉,潔白的眼睛──在動物如此這般迸湧而出之中,看見了神的顯現。
「牠受傷了,沒辦法逃,牠發現牠了,牠會死掉。」好幾個月,我聆聽著這類的句子。那個傍晚,一隻流浪蜘蛛(araignée errante)──「一隻狼(lycose)」,她說──將一隻天牛從一根蕨類的莖後挖了出來。「牠會為牠注入劑量致命的毒液,牠會吞了牠。」她跟木尼葉一樣,很懂這類事情。是誰灌注給她這些直覺的?這是古時候的知識了。有些人就算沒有完成學業,大自然的智慧仍然充盈、感孕著他們。他們是通靈人,識透萬物間怎麼布置安排的一個個謎;與此同時,學者還在研究這座宏偉建築的其中一個房間。
她在灌木叢裡閱讀。她理解鳥,理解昆蟲。沙茅草拂開的時候,她說:「這是花朵對著它們的神──太陽祈禱。」她拯救被小水溝的水沖走的螞蟻、被荊棘絆住的蝸牛、翅膀受傷的鳥。在一隻金龜子前,她說:「這是紋章上的幾何圖案,牠值得我們崇拜,牠鑲嵌在遊戲之中。」有一天,在巴黎聖塞弗杭教堂(Église Saint-Séverin)的廣場,一隻雀鳥棲落在她頭上,我捫心自問:我配得上一位鳥類將她當成枝椏棲息的女人嗎?她是女祭司,我追隨著她。
我們曾在傍晚的森林生活。她的養馬場在朗德省占地十餘公頃,位在一條小路的西側;車輪的印痕對她來說,似乎是隱居生活最好的保障。她在森林邊界的後方整理了一棟松木小屋。一泓小池塘構成了這塊土地與房屋的軸心。綠頭鴨在池塘休息,馬在池塘喝水。周遭,濃密的草刺穿了動物們踩啊踩的沙地。小屋裡全部的設備:一座暖爐,一些書,一把雷明登700步槍(Remington700),泡咖啡的器材,一面喝咖啡時使用的遮雨篷,一套散發植物汁液氣味的馬具。一條法國狼犬(bas-rouge)守衛著這方王國,牠靈敏矯捷,跟貝瑞塔92手槍(Beretta 92)的擊錘一樣蓄勢待發;面對有禮貌的人,牠則會展現愉快的心情。牠會殺了第一個不速之客。我逃脫得千鈞一髮。
偶爾,我們會坐上沙丘。海洋脈動著暴狂,浪濤永不倦厭,破碎崩塌。「海洋與大地之間一定有古老的糾紛。」我說著類似這樣的話,她沒有在聽。
我把鼻子埋入她散發黃楊氣息的頭髮中,聽她細細闡述她的那些理論。人類在幾百萬年前出現在地球上。飯桌擺設妥當了,森林鋪好了,動物晃闖遊蕩,人類就不請自來了。新石器革命與所有革命一樣,敲響了恐怖統治的鐘。人類宣布自己是生物中央政治局的老大,空降到層峰,想出一大堆教條來合理化自己的支配統治。所有人都捍衛著同一樁利益:他自己。「人類就是上帝的宿醉!」我說。她不喜歡這些說法。她罵我專講些沒屁用的話。
在圖博的沙丘上,我跟理奧述說的想法,也是她啟蒙我的。動物,植物,單細胞生物,新皮質(néocortex),這些都是同一首詩的碎形(fractale)。她跟我說起了太初的濃湯:四十五億年前,一團基本的材料在水體中翻騰攪動。「一切」早於「部分」。在這羹湯之中,有個什麼誕生了。一次分離發生了,然後,形式分歧了,各自各自複雜起來。她敬愛一切動物,視牠們為同一面鏡子的破片。她拾掇一根狐狸的牙,一綹鷺(héron)的羽毛,一塊烏賊的喙;凝視著她的這些碎片 ,她呢喃:「我們都起源於『同一』。」
沙丘上,她跪著,說:「牠會回到牠的隊伍裡,牠被佛甲草(orpin)的汁液吸引了,其他成員則輕輕鬆鬆就走了過去。」
這次是一隻螞蟻。牠朝一個黃色的蓓蕾拐了彎,然後回到螞蟻的行列中。對動物這些不值一哂的零瑣,她的無限柔情從何而來?「從牠們願意圓滿事情,」她說,「從牠們精確無比。我們其他人,並不認真。」
夏日,天空湛藍。風凌亂著波濤,白色的泡沫誕生在渦流中。空氣溫熱,海洋瘋狂,沙地嫩軟。海灘上橫陳著一條條人的身體。法國人變胖了。各種螢幕惹的禍?六○年代開始,各個社會都坐了下來。自從模控學(cybernétique)帶來了劇變,圖像就在靜止不動的身體前輪番播放。
一架飛機飛過天空,機尾拖著一幅婚外情網站的廣告。「大家應該會想像,機師飛越海灘,看見自己的老婆跟在這網站邂逅的一位先生躺在一起。」我說。
她凝望海鷗在風中衝浪,風持續推送緩緩的波濤。陽光劇烈。
我們踏著柔軟的小徑回到小木屋。此刻,她的頭髮聞起來像教堂的蠟燭。對她來說,森林輕響著意義豐繁的窸窣聲。樹葉就是一整套字母。「鳥類不會為了虛榮而啁啾宛轉,」她說。「牠們鳴唱愛國歌曲或是小夜曲:我在我家,我愛你。」我們進到小屋中,她開了羅亞爾河谷的葡萄酒,那是一支屬於沙子、屬於薄霧的酒。我暢飲欲死,這澄紅的毒液腫脹了我的靜脈。夜在我體內升起。一頭倉鴞(chouette effraie)尖聲嘶鳴。「我認得牠,牠是附近在地的,牠是夜晚的精魂,死掉的樹的總司令。」這是她的一項執著:重新分類生物,揚棄林奈(Linné)以親緣遠近為依歸的結構方法,改採一套橫跨類別的秩序,不分動物與植物,以性情來分類。因此就有貪吃的天賦──鯊魚與食肉植物共享此一天分;有彈跳的才華──這是蠅虎(araignée sauteuse) 或袋鼠的特質;有長壽的異稟──此乃烏龜或巨杉(séquoia)的正字標記;有隱藏的天才──由變色龍或竹節蟲體現。這些生物被賦予了同樣的才能,這個時候,牠們並不隸屬同一門就沒什麼大不了的。她由此推斷,一頭杜鵑鳥與一隻吸蟲(douve),牠們雙雙通曉鑽營的技藝,也都對自己的苦主有洞察入微的掌握,牠們彼此之間,也就比牠們和各自親族某些成員相比還來得更像同類。在她眼前,生物世界展現了琳瑯滿目的戰爭策略、愛情策略,以及行動策略。
她起身將馬引導進馬舍。那是一幅前拉斐爾派(préraphaélisme)的圖景:一位緩慢、強硬、明亮、精確的女人走在月光下,後面跟著她的貓、一頭鵝、一群沒有戴上籠頭的馬、還有一條狗。諸般璀璨的星座之下,還差一頭豹。一眾成員魚貫行走,抬頭挺胸,沒有摩擦,沒有聲響,不相碰觸,成一無瑕直線,完美保持距離,對要去哪裡胸有成竹。一支井然有序的隊伍。牠們的女主人哪怕顫動得再怎麼輕微,動物們都會像一道道彈簧一樣開始動作。她是亞西西的聖方濟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的姊妹。如果她信上帝,她會加入貧窮與死亡的修會,一種屬於夜晚的、神祕主義的共產主義,成員不透過神職人員,而直接對上帝說話。再說,她與動物契闊談讌、交誼來往,這本身已是一種祈禱。
我失去了她。她不想要我,因為我拒絕毫無保留、毫無選擇地,委身愛戀大自然。我們原本會在一塊廣袤的地產上、一座深邃的森林裡,專為凝賞動物而留的一間小屋或一座廢墟之中生活。幻夢消逝了,我望著她逐漸遠離,她的離開與她邁步前行的時候一樣輕輕緩緩,夜幕垂落森林,她的動物翼護在她的身邊。我重新上了路,增加著旅行,跳下飛機趕搭火車,在一場又一場的分享會上,(用自信不凡的語調)尖聲叫嚷人類最好不要再躁動不安了。我踏遍地球;每次我邂逅一頭動物,朝我顯現的,都是她消逝的容顏。我四處追蹤著她。在莫澤河畔,木尼葉跟我談起雪豹時,並不曉得他是在邀請我與她重逢。
如果我遇見雪豹,我唯一的愛就會顯現,與雪豹合而為一。我將每一次的
邂逅都獻給那散亂凋零的,我的愛的回憶。

本文選自 木馬文化《 在雪豹峽谷中等待 》
「這世界需要蹲點靜候。」作者去青藏高原拍雪豹,在貼近天空的地方蹲點,起初懷抱著非得要看到雪豹的心情,沒想到最後在等待雪豹的過程中,他對於旅行、人生、世界,都有了新的態度和體會。「我學到了,耐心是一項無上的美德,最優雅,也最為人遺忘……牠吸引人在舞台前坐下來享受表演,哪怕舞台上只是樹葉在顫動。」「等待是一種祈禱。有東西翩然前來。如果什麼都沒出現,那是因為我們不懂觀看。」
◎書籍資訊:https://pse.is/3j7vze
◎ 更多戶外資訊請見: 山林野趣粉絲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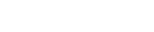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