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帳篷背在身上,就能找到安定與歸屬?

我以為把帳篷背在身上,就能得到安定與歸屬。原以為隨著日出與日落,隨著月圓月缺,便能知道生命為什麼要給我這樣的課題。
凌晨四點鬧鐘響起,窸窸窣窣地從睡袋起身,MSR Hubba Hubba帳篷透進微微灰色的天光。我瞇著眼睛,伸手摸出前方小袋中的頭燈戴上,穿起左手邊Patagonia的羽絨外套,套上塞在睡袋末端乾淨的襪子。半身坐起,頭剛好頂到帳篷的頂部,溼溼冷冷的內帳提醒我昨晚紮營在湖邊,霧氣正寒。睡前那瓶放在睡袋右邊的熱水還是暖的,比體溫熱上一度,正好入喉。
我愣愣地坐著,看著頭燈投影在帳篷裡自己的影子,這一天的二十五公里又要開始了。
長程徒步是以動輒幾十天、距離以幾百公里、爬升陡降以好幾百個一○一疊加起來計算。從A點到B點的線性移動,我在出發前原以為這會是一個極為浪漫的旅程,把家背在身上,把時間過在腳上,從步伐裡踏出每一天。
真的到了步道,我好累,真的好累。走了一整天,大家放下背包後總是親暱地挨著肩坐,揉揉雙腿換上涼鞋,互相倒杯水抱怨剛剛越過的那顆磨人山頭。我卻是憋著氣馬上把背包翻開,拉出帳篷,忙不迭地自己一個人搭起帳來。蹲下來目測營地的水平度,整地撿拾石塊樹枝,確認日落角度,算好隔天太陽升起的方向。非得要搭起帳、鋪好睡袋後,才讓自己喘第一口氣。
就寢前,在帳篷裡就著頭燈,確認今天行進的距離、速度,以目標的遠近來計算明天的爬升、可能的營地與日落時間。一一清點早中晚餐的分配、存糧的份量、凍壞的濾水器怎麼修理、相機記憶卡的照片要轉到手機備份,還有右腳大拇指那個莫名的水泡。這樣那樣,一天結束又一天開始,把家拆掉又把家搭起來。我躺下來,聞著超過十幾天沒有洗頭的頭皮味,我正在想。
我為什麼在這裡?我在做什麼?
我以為把帳篷背在身上,就能得到安定與歸屬;透過長途徒步,就能明白自己的恐懼與遲疑。我原以為隨著日出與日落,隨著月圓月缺,便能知道生命為什麼給我這樣的課題,或為什麼人生總是這麼難,但其實,即便走到這裡,我的恐懼仍交織著遲疑,神諭與天啟並沒有壓倒性地出現。什麼是想要?什麼是需要?誰被誰選擇?我是否只是個選項?步道並沒有透過星星告訴我答案。
今天醒來,我愣愣地坐著,看著頭燈投影在帳篷裡自己的影子。
也許啊,我不能得到什麼噢。我突然這樣想,也許走完了約翰.繆爾步道這三百四十公里,我還是原來的我,既沒有什麼體悟,也沒有方向,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我可能仍然只是其中一個選項。那也沒有關係,太陽等等就會從這個角度升起來,日落前我仍然要把帳篷搭起來。
在這條步道上,我跟我自己走在一起,我就是我自己的家。我已經有能力面對我的不安就只是那不安,我的牽掛就只是那牽掛,那不是我。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在這裡。

本文選自 遠流出版《山之間》一書。
也許通往山林的路徑,就是通往心的方向。作者 山女孩Kit 帶大家越到山的另一面,窺看自己的脆弱、誠實,以及從山裡尋獲的勇氣,還有活得最像自己的那一面真實。山,讓她成為更好的人,保有對生活最終的信念與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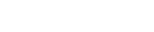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