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將愛之人輸給山的人們 來自登山亡者家屬的痛心告白

人在山上有許多種死法:凍死、摔死、餓死、累死,死於雪崩、落石、落冰,以及高山症這種無形攻擊引發的腦水腫或肺水腫。當然,墜落永遠都可能發生。地心引力永遠不會忘記或者疏忽職守。法國作家克勞岱爾(Paul Claudel)說得很好,我們沒有翅膀可飛,但始終有足夠的力量墜落。
如今每一年都有幾百人在世界各地的山區遇難死亡,還有幾千人受傷。歷來光是白朗峰就奪走一千條人命,馬特洪峰五百人,聖母峰大約一百七十人,K2(喬戈里峰)一百人,艾格峰北壁六十人。一九八五年,光是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區就有接近兩百人死亡。
我在世界各地都看過山難死者。他們集體葬在山區小城的墓地或基地營的臨時公墓裡。在高山上,死者的遺體常常無法運下山,或甚至連遺體都找不到,所以很多死者只以物品或象徵代替:用螺絲把名牌整齊地釘到岩石表面、名字刻在巨礫上、石頭或木材粗略做成的十字架、玻璃紙包起的花束,還有一貫的悼詞與之相伴,這些悼詞頻頻執勤,且每次值勤時的力道及哀切都不曾或減:此處躺著……於此處墜落……紀念……所有壯志未酬的生命。
對於山難死者,我們很容易惋惜或頌揚。但應該要記住的(常常被遺忘),是死者拋下的人。那些父母、子女、丈夫、妻子和夥伴,都把所愛的人輸給了山。所有裂了一塊有待補回的生命。經常上山冒巨大風險的人,應該被當成極度自私,或不憐惜愛著他們的人。我最近在一場酒會上遇到一位女士,她的表弟在前一年墜落身亡。她對此感到憤怒又困惑。為什麼他非得爬山不可?她開口問我,但並不想得到答案。為什麼他不能就去打網球,或者釣魚呢?讓她更憤怒的是死者的弟弟還繼續在爬山。她說,她的姨母和姨丈失去一個兒子已經夠淒涼,可是另一個兒子卻還繼續投入讓他哥哥喪命的消遣。或者,至少一星期前還在登山,結果摔下山跌斷兩條腿。她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很高興,她說,因為她猜想他從此就不會再爬山了吧,這樣他的命就保住了,沒辦法再—那麼自私了,她餘怒未消地咬緊牙關嘶聲說道。我後來聽說,他雙腿恢復了,石膏拆除不到一個月,就又上山了。
遇到這樣的情形, 難免讓人覺得是某種邪術或催眠術在作祟, 登山之愛變成了某種類似洗腦的狀態。這是登山活動黑暗面的一個例證,提醒人們登山潛在的高昂代價。不可否認,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的性命賭在山坡上或崖壁上。登山並非天命,不一定得發生在一個人身上。
現在我充分體認到, 死在山上並沒有什麼內在的高貴可言, 反而有種令人深惡痛絕的浪費。我大致上已經不再冒險。需要綁繩索以策安全的路線,我已經不太爬了。我發現,待在高山上而且冒的險比,隨便說,在城市裡過馬路更小,是絕對有可能的。而且我現在也更容易害怕,恐懼的門檻已經大幅降低。那種血脈賁張、令人反胃、隱約激發性欲的真實恐懼,近來會更快控制住我。五年前我會高高興興沿著懸崖邊緣走,現在則會敬而遠之。像大多數登山客一樣,現在對我來說,高山的吸引力更多源自美麗而非艱險、源自享受而非恐懼、源自驚歎而非痛苦,以及,源自活著而非死去。
然而事實是, 很多人仍舊禁不住誘惑而到山上冒險, 仍舊死於山間。法國境內的霞慕尼可能是登山愛好者人心目中最偉大的聖地,是我所知道僅有的一個旗杆上裝著鋼釘倒刺以免有人攀爬的地方。那是人口密集的小鎮,公寓、教堂和酒吧全擠在阿爾卑斯山區的一道峽谷裡。看到小鎮坐落的位置總是讓我驚訝。從日內瓦陡急的山路蜿蜒而上,你不會想到那裡還有足夠的平地可以建一棟房子,更不用說是小鎮了。可是居然就有這麼一個小鎮,就位於山谷之中。鎮上四面八方都是岩石斜坡,沾上冰河水,把人的視線帶往白朗峰閃閃發光的銀色峰頂,以及聳立於每一道天際線上的鐵紅色岩石尖頂。
霞慕尼每年夏天的登山季中, 平均每天都有一人死亡。他們無聲無息地死去,不會有死者的朋友在酒吧紅著眼睛緊盯著某些空位,也不會有氣喘吁吁在炎熱的街道上呆呆走著一臉哀戚的父母。唯一的線索是小鎮上空縱橫交錯的救援直升機螺旋槳發出的轟隆聲。每回有直升機飛越, 酒吧的人都會抬起頭來, 簡略判斷一下是要往哪邊飛。

本文選自大家出版《 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 》一書,本書試圖解釋一座山如何能夠全然地使一個人深深著迷,這樣鬼斧神工的龐然大物竟然能夠使人類強烈地愛慕。因此書中要檢視的不是人要用什麼方法登山,而是如何想像自己如何登上山岳,以及對山岳的感知。
◎ Photo by 杜立德
◎ 書籍資訊: https://bit.ly/2ShuUmy
◎ 延伸閱讀:登山活動因人類想像力而更具魅力 躍升新世代冒險挑戰產業
◎ 更多戶外資訊請見:山林野趣粉絲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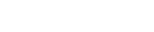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