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帶葬禮
民法第272條第一項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
天空彷彿能預測我們的情緒。
長廊裡,地磚紛紛然飄落溼溽的痕跡,所有人都拖著皺縮的褲管,沉重而失神地前進。入口處搭蓋了白色布簾,我接過一只「零」形緞帶,貼在心口上,與一群不太熟識的面孔湧進會場,大多都是遠房親戚,最遠還有從南部特地趕來的。這景象並非初識,過去我曾是參與的一分子,儀式中得穿著黑色大衣,如魂魄俱散之幽靈,制式化地向會眾鞠躬致意,因為雙眸空洞、眼神迷離,讓我無法辨明他們的表情。如今總算可以看見了,我們和F共同連著一條或粗或細、或深或淺的線,在盡頭處繫著盛放的花蕊,像無數個回憶繩結,上頭記載彼此之間的故事和關聯。
作為F的晚輩,雖然住得很近,平時卻無甚交集,只有特定節慶才會見面,見面時頂多也是寒暄幾句,隨後F便和父親喝酒聊天去了。自始至終,我們好比君子之交,關係可能還比水更淡、比風更薄,但每次拜訪F都以佳餚款待,無論親疏遠近,連職場也不分距離。所以當他的企業夥伴近前獻花時,用敏捷步態試圖掩蓋難言的悵惘,但悲傷很輕,捧在手上像快被吹落的尾羽,一旦放下就飄散而去。他們轉身走出會廳,與其連結的繩線被逐漸拉長、透明,大門關起的瞬間,像把利刃劃清彼此的範圍。
然而,有些關係會像「連帶債務」(基於契約明示或法律規定,使多數債務人間發生牽連關係,外部對於債權人各負全責,內部平均分擔的債務),譬如手足或兒女。F的兄弟姊妹們聽聞消息後,包下整台遊覽車,和其他遠房親友從南部趕來台北,為了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好好道別。他們因為長期務農,皮膚曬得黝黑,臉上皺紋清晰可見,即使年逾古稀,但身子看起來卻健壯如昔。印象中我完全沒有聽說或見識他們哭泣過,或許在那種年代裡,生活單純平凡,不如瞬息萬變的台北,把關係塑造為能隨時替換的日用品,連情緒也開始動盪不安。起初,他們神色還算泰然自若,悲傷仍潛於心底的暗流,硬生生被壓抑著,等待噴發或召喚。
當司儀沉沉地宣布,請大家離開座席,手持一朵黃色小花,列成縱隊,依序走進會台後方的隔間。和F關係親近的人都摀住嘴,眼角汨汨掉落苦痛的水晶,他們彎著身子從另一側出來,腳步踉蹌,需要彼此攙扶才能勉強站立。哀鳴和啜泣聲溢滿會場,淌出大廳,溶入迷濛黯淡的空氣,每次回憶那些場景,總是感覺有什麼東西從深淵冒上來,被妥當地分配,然後逐漸淡開。進入隔間裡,輪到我把花輕輕種在F的身邊,在大片金色草原,遍地死寂於是萌現生機。世界本該混濁而枯槁,被我們「分擔」一些晦暗之後,終於有光透過來,凝結未乾的眼淚,讓本應腐朽的花瓣逃脫凋零之命,昇華直至永恆。
儀式過後眾人紛紛離散,有些步伐闊綽、背影瀟灑,有些原地踱步、陷入漩渦一般,但F的手足仍像接連綁縛的平結,互相倚靠著。比起拐杖,似乎這樣更能夠支撐被重擔壓得彎駝的脊骨,數個佝僂身軀在綿雨將息之境猶若斷木,外表紋理斑駁、蒼白衰老,內中卻飽含實心,隱隱然萌現生意。直到陰雲散開,一切就會好起來。
F的女兒、女婿抱著紙造的啤酒塔,和一輛迷你版賓士車,說要拿去燒,還說燒的時候必須張開手,數人圍成一個大圓形,圈子不能有縫,因為會被偷。我原先對這種習俗半信半疑,但他們講起話來竟有莫名的決心,彷彿也連帶影響了我,像是聽完父母編造的床邊故事後,感覺他們能夠理解那些說不出口的擔心,於是在關燈之前,就把恐懼交給他們,好讓自己安穩抵達夢的邊境。我想像啤酒罐與紙車慢慢崩解、最終被火舌吞沒的樣子。從這裡失去的,到那裡就變成祝福了。
陽光已經剖開天空,推移兩旁陰鬱晦暗的雲朵,金粉翩然落下,翅翼透薄的蝶自遠方帶來寬慰,我們都是溺水者,只是被打撈上岸之後,取回呼吸的技能連帶遺忘原本的身分。有什麼東西已然逝去,任何人都無法追及。光在水痕裡汨汨流動著,像一片海,大雨止息,餘剩的風失卻破壞力,四境安好如初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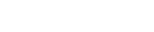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