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薪水那麼高,搞什麼工會?
【編按】本文為去年(2021)五一勞動影展,「不是金飯碗」放映專題座談「你們薪水那麼高,搞什麼工會?」紀要。今年(2022)影展將於 4 月 22 至 30 日,在台中、高雄、台南、嘉義、桃園、新北巡迴放映;完整片單、場次及影片詳細介紹,可至影展官網查詢。
逐字稿:陳知妤、廖方瑜、林若芷、李品蓁、王浦郡、張凱峻、駱浩昀、陳郁勛、徐慧真、劉裕安

文/林名哲(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
去年此時,我收到邀約,出席五一勞動影展的「你們薪水那麼高,搞什麼工會」座談。座談會由陳淑綸(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主持,與談人除了我,還有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陳信儒,以及身兼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研究員的陳柏謙。
雖說「薪水這麼高,搞什麼工會」這個問題略帶戲謔,卻是不少人心中的疑惑。有很長一段時間,提到工會運動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一群弱勢、低薪、備受壓榨的勞工,為了擺脫困境只好集結抗爭的經典情節。若將故事主角置換成高收入、看似光鮮亮麗的從業人員,總覺得格格不入。別的不說,就連我身為科技業工會的組織者,每當自己說著「加入工會、保障權益」時,回頭看看身邊年薪百萬的工程師會員,也不禁心虛。高薪從業人員有更多專業能力與社會資本,能輕易透過勞動力市場交換到符合身價的勞動條件;若單純考量經濟利益,他們實在不需要透過工會乃至工會組織者的支援,就能滿足需求。
話雖如此,去年那場座談辦得成,代表高薪「勞工」的工會不只存在,而且並非少數。曾幾何時,這群高收入,看似光鮮亮麗的從業人員也組織起來,這是為什麼?座談中,主持及與談人們做出了說明。
有錢也要有命花:從反對過勞中誕生的工會
開場,主持人陳淑綸介紹,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之所以於 2017 年成立,主要是為了爭取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以對其工時進行限制,解決嚴重的過勞問題。經過工會爭取,2019 年 9 月 1 日起,住院醫師適用《勞基法》,但同時卻也適用第 84 條之 1,豁免單日正常工時 8 小時、單週正常工時 40 小時的規定,單月工時上限可達 320 小時。陳淑綸說,自己看到單月工時上限 320 小時有「挫一下」:「320 小時各位算數學除除看,很可怕的,就等於一週 80 小時,一天 16 小時!」對他的驚嚇,醫師工會的工作人員回應:「先求有再求好,總比沒有、不寫那個上限好。」
接續陳淑綸的開場,醫師工會理事陳信儒進一步說明,單日工時上限 16 小時的意思,是連續工作不得超過 16 個小時:「以前會有一些連續值班,第一天是 24 小時,繼續接明天上班的狀況;但現在已經無法這樣做,因為有兩個規範,一個是總工時,另一個是連續工時。」而這個遠高一般勞工的工時上限,其實只規範住院醫師,主治醫師不適用。陳信儒說,自己雖然還掛住院醫師頭銜,但已拿到專科醫師執照,不再適用《勞基法》:「醫院發給我聘書的時候,因為我的頭銜還是住院醫師,所以他們把 84-1 條寫在我的聘書上面。一個月後,他們發現這件事情,就把聘書收回去,那一頁全部抹掉。工時 320 小時怎麼可能會超過,對不對?但這樣,為什麼還要把我的聘書收回去重寫?」

從上述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醫師雖然是社會上,收入較高的專業工作者,但依然有像工時過長這樣,顯著的勞動權益問題。而我自己服務的電資工會,當初成立的緣由,也是業界嚴重的過勞,危及了勞動者的生活、健康。
電資工會成立於 2011 年。該年,一位HTC(宏達電)的工程師疑似過勞死,被不少媒體報導。在影展放映的《機器人夢遊症》一片中,觀眾可以看到,該名工程師被發現倒在租屋的電腦前,禮拜六凌晨身亡前還在工作。這個事件,可以說是電資工會成立的導火線。雖然HTC始終沒有承認那是過勞死,可是大家看到這樣子的新聞,同業間都心有戚戚焉,開始反思這個工作,薪水也許有比其它行業多一點,卻也承受很長的工時、極高的壓力。在焦慮及危機感下,一批工程師於是透過網路號召成立工會。
趨勢:白領專業人員勞動條件下滑、勞工認同上升
醫師、工程師開始覺得自己的工時過長,徵顯出醫療及科技產業,勞動條件在逐漸下滑;相應,則有愈來愈多的從業者,認同自己是勞工。
像工程師這種白領、專業技術人員,大家在過去會想像,他們的勞動意識比較薄弱。我自己讀大學的時候,很多高中生選擇電機或資工為前幾個志願,憧憬有機會成為「科技新貴」(這個詞好像慢慢成為歷史,現在幾乎被淡忘)。到了我唸完書出來就業,整個局勢、風向改變。大家進入這個產業,發現雖然薪資待遇相較其他產業稍高,但也無法讓人像以前還有分紅配股時,可以工作個 20 年就退休。當這種機會渺茫,大家會認識到自己其實不過是個錢賺多一點、可以吹冷氣的打工仔,工作的負面部分於是凸顯出來。以我自己的經驗,電資工會成立到現在的 10 年間,勞動意識有比較被承認。

至於醫師,陳信儒說,社會大眾或許認為醫師都是菁英,但這群人遇到勞資爭議,還是會跟一般勞工一樣慌了手腳。醫師工會就曾幫醫師處理過代訓約違約的問題,也就是醫院將醫師送去別家醫院受訓,同時簽不平等契約,規定你受訓回來要「返還」更多的工作時間,否則就要給付高額賠償金。類似這種狀況,醫師本身沒有處理經驗,也不曾受過相關訓練,就需要工會協助。
機師也不例外。陳柏謙提到,2019 年機師工會罷工,主要訴求是調整紅眼航班、改善飛安;但航班安排是公司獲利的命脈,資方當然不願輕易退讓,甚至在談判過程中,抓住一名幹部的小辮子,逼他退出工會運作。此時,即使是月薪數十萬的機師,都會發出「沒辦法,這就是受僱於人」的喟嘆!針對各種高薪專業人員在職場上的身份認同,陳柏謙認為:「很多時候我們去看,不是用藍領或白領,不是用他的薪資一個月領兩萬還是一個月領二十萬;而是他在這個職場裡面,有沒有對他自己的勞動時間有控制權?他有沒有感受到自己是被主宰的、被剝削的、必須聽命的那一群?那才是要不要組工會的關鍵。」
工會與團結:讓勞工看見彼此、克服矛盾
不過,有了勞工意識是一回事,工會組織起來,運作又是另一回事。尤其,在產職業工會的框架下,勞工不像在企業工會,有一個所有人會「自然而然」投入,視彼此為共同體的範疇;所以,工會必須花更多力氣去處理內部差異,打造會員的集體認同。
例如,陳柏謙介紹,高教工會的會員,來自八、九十間不同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勞工的職種,有專任教師、兼任教師、研究助理、教學助理跟職員。職員,分編制內、編制外。公立跟私立學校,適用的人事法規又不一樣。專任的正教授,月薪可以達到十萬。兼任教師以鐘點費計薪,講師級每小時約六百塊左右。由於專任缺愈來愈少,很多「兼任教師」其實是全職工作,每學期必須在全台灣,北、中、南各地不同學校「兼課」二十幾學分,才能賺到一個月大概四萬塊的薪資,而且寒暑假沒有收入:「我們遇過很多,開學後每週都在環島旅行,就開著一台車,從北部教到南部然後再回去。」
在工會的會員組成極為多元、彼此高度殊異的狀況下,內部難免出現矛盾。陳柏謙坦承,高教工會剛開始爭取大學兼任助理適用《勞基法》時,許多專任教師會員並不贊同。而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醫師之間。陳信儒說,在醫院裡,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通常有一定的指揮、管理權力:「所以當初在討論要不要把醫生納入《勞基法》的時候,政府都會丟出一個問題:你們要主治醫生還住院醫生納?這其實是分化的手段。因為主治醫生覺得一旦納入《勞基法》,下面的人幫他做事的時間就縮短了,所以有一票主治醫生不要,醫院當然也不要。政府不要淌這個渾水的話,先這樣丟,你們自己就會吵架。還有公務員的醫生、約聘的醫生、軍費的醫生,它會一直問你,《勞基法》到底要適用在哪個身份的醫生上?」
就此,陳信儒反思:「一開始,大家覺得這個問題很有道理,適用對象要講清楚。但後來回過頭想:奇怪,《勞動基準法》不是對勞工能接受的工作條件跟指標,訂定一個通用的底限?怎麼會因為一個工人或勞動者的身份有區分,變成要討論適用不同對象?一個公務員醫生跟一個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難道會因為他的身份改變,能夠承受的勞務、工時不一樣嗎?其實我們希望全部都納入《勞基法》,但現階段就是有困難,因為主治醫師的意見分歧。」
所幸,工會還是有可能,克服勞工、會員間的矛盾。在提到高教工會的許多專任教師會員,起初反對大學兼任助理適用《勞基法》後,陳柏謙接著表示:「這個要如何處理,就是產業工會的功能。要說服其他的會員,這在勞動權益的價值上是必要的,即便在過程中可能會喪失一部分。可能看起來會有矛盾在,但不代表沒辦法去說服,找到共識,把陣線建立起來。經過說服,很多專任老師其實願意去協助。在這樣的過程中,矛盾透過內在的方式轉化。」
進一步,陳柏謙根據高教工會的組織工作經驗歸結:「因為產業工會的型態,我們看到在會員裡面,有薪資十萬左右的正教授,也有我剛剛講到的弱勢,領時薪的華語教師、TA。其它很多產業也是這樣,像名哲講電子業裡面,工程師跟生產線作業員就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如果透過同一個產業工會去框定團結的邊界,其實你是讓同樣會受到這個產業影響的一群人,有機會在工會裡面看到彼此。這跟企業工會不太一樣,企業工會如果它的工作場所是比較緊密的,就算你不特別怎樣,勞工也都可以相互看到。但是產業工會的運作,如果沒有特別設計,不同學校、職種的人,他其實不會看到彼此;這個時候,就必須透過一些機制,讓不同職種、不同學校也可以看到彼此。」

後疫情時代,把勞工重新「連上線」
回顧去年座談,上述對「為什麼搞工會」的答案,基本不脫集體協商、改善勞動環境等面相。眼前人類遭逢百年大疫,關於工會存在的意義,我認為可以有更深入的答案。疫情期間,世界各地都出現程度不一的封城、隔離,人們被迫關在家中鮮少出門。儘管如此,為了維持營運與獲利,企業逐漸適應,遠距工作成為新顯學。往好處想,連最保守的公司都不得不邁開大步迎向數位化,或許能拋棄不合時宜的沉痾。但往壞的一面看,企業實際演練更多將勞務分割、外包,同時又能透過網路科技進行監控的手段。也就是說,疫情造成人與人之間物理上的隔離,但資本汲取勞動力的管道並未因此中斷,反而更為精進。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全雲端工作搭配突破時空限制的全天候監控,會成為許多人的勞動日常。
資本的力量總能突破各種隔閡,但人與人之間斷掉的連結該如何修復?其實,工會的核心不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同一工作場所、相同職種甚至同樣產業的勞工,透過聯繫和對話,或者相濡以沫、或者同仇敵愾,加深彼此連結最終成為緊密的共同體。若說,疫情肆虐造成的物理隔離,以及資本為控制勞動力加諸的制度隔離(想像一下位於美國的科技公司與他們遍布全球、數以百萬的眾包「勞工」之間的關係)是當今切斷勞工之間連結的兩股力量;那今日的工會,不只要扮演集體協商的角色,更要扮演將分散、分化的勞工重新「連上線」的重要功能。
正巧,今年五一勞動影展當中,一半以上的影片,都在說那些被疫情、被資本切斷連結的人們,如何重新建立聯繫的故事。我承認,身為組織工作者有改不了的懷舊情結,總試著用歷史上工會的經典故事,來重述眼前的處境。然而世道變化之快,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存這個議題,絕對不只一種答案。唯一肯定的是,只有一起面對、一起思考,我們才能一起找到解答。邀請大家參加今年以「搏生存」為題的影展,作伙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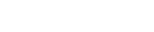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