咥 麵/兩木金
兩木金
一說起陝西,你肯定會想到那幾句民謠:“八百里秦川塵土飛揚,三千萬兒女齊吼秦腔,咥一碗黏麵喜氣洋洋,沒放辣子嘟嘟囔囔。”
陝西人愛吃麵,天下聞名。我是陝西人,自然嗜麵如命。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陝西人,你請他吃飯,一試便知。你問他:“夥,我請你吃飯,你說吃啥?”如果他豪不猶豫,脫口而出:“咥麵!”那十有八九就是個陝西楞娃。你就是請他去海鮮城吃大餐,酒足飯飽之後,他還喊服務員過來問:“女子,你這有麵嗎?”那毫無疑問是個老陝。
你去陝西關中農村遊玩,常會看到一老者或者少年端一個比腦袋還大的大碗公,蹲在門前一大石凳子上,挑起寬如褲帶、長有幾米的油潑扯麵,雙眼瞪得溜圓,額頭青筋暴起,狼吞虎嚥,吃得熱汗如雨。你問之:“鄉黨,早上吃啥飯?”對方必定回你一句:“咥麵!”“午飯呢?”“還咥麵!”“晚飯呢?”“還咥麵!”
陝西人對麵的熱愛已經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陝西關中平原盛產小麥和玉米。現在人們生活條件好了,不缺糧食。玉米多用於工業生產,不再是人們餐桌上的主食。小麥粉做成的麵食就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越吃越愛、咋吃都不膩。
我自幼喜愛麵食,但那時候家裏窮糧食少,白麵粉非常昂貴。大多時候,家人一日三餐吃用玉米粉做成的窩頭和攪團、魚魚飯,吃得人胃發酸,常吐酸水,又不耐飽,剛吃飽飯一會兒又饑腸轆轆,渾身乏力。只有在招待客人時,家裏人才能吃上一頓雪白的麵條。把那長長的麵條放進嘴巴裏咀嚼,再咽到肚子裏,那種醉人的麥香味始終在身體裏蕩漾,真的是回味無窮。我做夢都在想,啥時候能頓頓把雪白的麵條吃個飽,那肯定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生活。
直到我讀初中,家裏一直缺糧。每年過春節前,莊戶人家都要準備好過年用的麵粉。父親把金黃色的玉米和土灰色的小麥拌在一起,磨成淺黃色的混合麵粉,把它叫作幸福粉。母親用這種麵粉蒸出來的饅頭是淺黃色的,擀出來的麵條也是淺黃色的,吃進嘴裏,粗糙鬆散沒有嚼勁,麥香味淡了很多,不好下咽。吃著“幸福粉”,我享受著新年的幸福。
在困難年月,但凡農家婚喪嫁娶,不論貧窮富裕,主家擺宴招待客人,千篇一律都是湯湯麵。老家人也把它叫哈水麵,類似於岐山縣的臊子麵。廚師攤好雞蛋薄餅,切成菱形,把韭菜或者大蔥切成碎末,紅蘿蔔切成細絲,拌上泡好的黃花菜和黑木耳,再熬制一大鍋湯,倒入菜油,將切好的各樣菜倒入湯內,放進紅燒肉片,調上辣椒、鹽、醋。這一大鍋臊子湯就做好了,湯講究“煎稀汪”。麵條可以是機器壓制的,也可以是手擀細長麵條,講究“薄筋光”。麵條煮熟,撈一筷子進碗,多澆臊子湯,麵少湯多,味道講究“酸辣香”。食者只吃麵,不喝湯。成年人一頓吃個二三十碗,還意猶未盡。外地客人不知曉此種吃法,端起瓷碗,吃麵喝湯,兩碗就撐得腹脹難受。
這種麵之所以被叫作哈水麵,是因為客人吃麵後碗裏剩下的口水湯並不廢棄,而是倒入大湯鍋,熬煮後,反復使用。吃麵後的髒碗也不洗,繼續撈麵澆湯,端上桌子,供客人食用。你用我剛吃過麵的碗,我喝你剛喝剩的湯。這種飲食習慣源於舊時吃食貧乏,莊戶人覺得將剩湯廢棄太過浪費,但終究是極不衛生,容易傳染疾病。
時至今日,農民富裕了,待客也吃炒菜,但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依舊是這一碗湯湯麵。儘管現在糧油便宜,但家鄉父老的飲食衛生觀念還未改進,仍舊要用回鍋湯。外地客人吃這哈水麵極香,問及做法,我是堅決不說此乃眾人的回鍋湯,只怕人家噁心。
記得我讀高中時,家裏過日子已開始“芝麻開花節節高”,一年比一年好過了,常年都是糧倉滿穀,再也不缺糧食吃了。白饅頭、白麵條,可以放開肚皮吃了。母親會做各種各樣的麵條,有寬麵、細麵、柳葉麵,有扯麵、棍棍麵、biangbiang麵,有包穀糝麵、南瓜麵、扁豆麵。我就算每天吃一樣麵,連吃兩三個月,都不帶重樣的,天天吃麵,依然樂此不疲。
我的高中學校距離家裏不算太遠。我每天早上騎自行車去上學,需要騎行三四十分鐘,才能到學校。我中午在學校吃飯。下午放學後,我再騎自行車回家,行至村口,老遠就看見母親站在家門口,望著村口我回家的方向,翹首期盼。看見我回來了,母親慌忙去煮早已擀好的麵條,幾乎每天都是同樣的麵條。我總要美美地吃兩大碗黏麵才能飽,天天如此,數年不變,我竟從未感到過厭煩。
我考大學那個年代,大學生的身份有兩種。一種是國家統招統分生,也就是公費生,另一種是自費生。兩種不同身份的大學生等級分明,學費和待遇有天壤之別。公費生學費很少,軍校、公安和師範院校學費都是全免的,每月還可以享受國家補貼,畢業後一般都包分配。自費生學費昂貴,沒有公費生那樣的待遇,心理上也會覺得比公費生矮一大截子。記得那一年我參加高考,距離公費生的分數線僅差一分。在那個三伏天裏,我去學校查看高考成績後,垂頭喪氣地回家。當時,身材瘦弱的母親正背著巨大的噴霧器,給雞舍噴藥消毒。母親熱得滿頭大汗,上衣幾乎被汗水浸透,努力挺起被沉重的噴霧器壓彎的腰,問我考上了沒有。我搖搖頭說:“公費大學差了一分,我不想讀自費。”母親一臉沮喪。我看出了她的失望。母親沉默了片刻,放下噴霧器說:“明年再來,咱堅決不能當農民,你吃不了那苦。媽給你擀麵。”我至今想起母親當時那失落的眼神,就忍不住心裏一陣酸楚,覺得很對不起她。
第二年,我發奮讀書,終於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西北大學新聞系,成為統招統分的公費生。那時候,公費大學生錄取率很低,考上很難。十裏八鄉,一年也出不了幾個大學生。考大學是我這樣的農家孩子跳出農門的唯一出路。母親不想讓我跟她一樣,一輩子在土裏刨食。得知我考上了大學的那一刻,母親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難以掩飾心中的自豪與驕傲,對我說:“我兒終於把事情弄成了。媽給你擀麵。”
上四年大學期間,每年寒暑假,我都回農村老家。我始終不喜歡吃炒菜,更討厭吃米飯。母親每日都換著花樣,給我做麵條吃。那時候,我常對母親說:“等我大學畢業,工作掙錢了,再也不吃麵了,頓頓要吃雞鴨魚肉。”母親說:“你要好好讀書,以後工作了,想吃啥都行。”
大學畢業後,我幸運地被分配到陝西電視臺當記者,有了一點經濟能力,可以吃好一些的飯菜,不用頓頓吃麵。我吃過山珍海味,也吃過饕餮盛宴,但最終還是厭煩了,總覺得不如端起大海碗,咥一碗麵條舒坦。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我都得吃一碗母親做的手擀麵。
我愛吃麵的飲食習慣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經久不變。有時候去外地出差,我兩三天不吃麵,便覺食之無味、人生無趣。妻子總說我不會享受生活,進城二十餘年,仍舊是個農民,一輩子就知道吃麵。我自嘲道:“我對麵條情有獨鐘、癡心不改。這體現了一種真誠執著的精神。這是做人做事的優秀品質。”
十多年前,父親因病去世。我把母親接到西安一起生活,但母親一直不習慣城裏的生活,說單元房就是牢籠,城裏人沒有人情味,鄰里間互不相識、互不來往,抱怨生活就像蹲監獄。每次來西安住一段時間,母親就嚷嚷著回農村老家,說那才是人過的日子,自由自在的。擔心母親回農村生活,一個人不方便,我就堅持不讓她回老家。母親思念故土心切,身體總會生出各種不適,有時候幾日水米不進、徹夜不眠。我帶母親去醫院檢查,除了血壓高和心臟有點小毛病之外,再無大恙,只得送母親回老家。說來也奇怪,一回到老家宅子,母親飯量也大了,晚上躺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睡眠異常香甜。
我已過不惑之年,雖然飯量明顯不如從前,最怕晚飯吃多了,撐得難受,夜不能寐,但始終沒有改變的,仍是對麵食的喜愛,甚至是越發強烈,幾日不吃麵,便渾身難受。每當嘴饞想吃麵時,我還是覺得天下美食,最香比不過家鄉的麵食,比不過母親手擀的那一碗黏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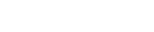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