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事

我總記不牢人名,也記不得電影劇情。連日日相處的同學名字,放個長假便全班忘光。畢業幾年辦同學會,有人還能背出每個人的座號,我腦中一片空白,像闖入陌生人的聚會。
更不用說電影或戲劇裡的細節了,不回想就變得模糊,再過幾天,劇情忘得乾乾淨淨,只殘留片段畫面的記憶。
我和大學時同班的女孩看過好多電影,去一間老舊的二輪影院,裝潢的合板脫皮褪色,灰塵填滿空氣的縫隙,呼吸和視線都沙沙的,不論商業片或藝術片皆有放映,但至今我記不清任何一部。
第一堂必修課的教室裡,人零星幾個,很多座位被物品示意占據,我兜轉幾圈,分不清楚究竟是空蕩,還是人滿為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前方的空椅,坐下之前,指著位置問身旁的女孩:「這位置是妳的嗎?」
她「啊!」了一聲,好像忘了什麼,左右張望一下,再對我擺擺手說「沒關係,沒關係。」
自我介紹一節課結束了,她的朋友還沒來,她百無聊賴地轉過頭來問我:「你也喜歡看電影嗎?我們可以一起去看!」
我心裡一直回想她剛才自我介紹過的名字,怎樣也想不起來,便點點頭,「我記得妳也喜歡看電影!」
我曾在網路文章中讀到,犯罪心理學家認為:案發現場若出現一把槍,目擊證言可信度會降低,因為證人的注意力,只會聚集在那把槍上。或許就像瑪利歐賽車遊戲那樣,臉上被後面玩家的「魷魷」潑上墨汁,視野變小、抓地力變差,不管去到多遠的地方,眼前只有那樣污濁的畫面,一切見證都變得殘缺可疑。
此刻我的腦袋裡充斥著槍聲,扣板機的零件勾撞,膛口火藥炸裂衝擊,劃破空氣的聲爆,子彈碰撞沒入。連續擊發,明明滅滅,我努力想要想起某件事時,腦中全是轟隆轟隆槍聲,視線顫動疊影,她的名字已經全面撤退。
至今我唯一仍記得清楚名字的是一個小學的男同學。
其實若不仔細回想,我常錯認他是在我後來更大年歲才遇到的同學──或許跟他是個早熟的人有關。
那時小學高年級剛分班,他是低年級曾同班過的同學,我們約好一起坐在最後一排,老師沒進教室之前,不像其他挺直背脊坐半椅的同學,我們開心地聊個不停,笑得東倒西歪。
新導師進教室以後,大家安靜下來,同學們一個個按導師指示上台自我介紹,他的手耐不住無聊,悄悄摸進我的褲子裡。我想努力記得大家,看清楚同學寫在黑板上大小不一的名字,但卻像發燒一樣,頭腦昏沉,粉筆字一一解體飛散。我張開腿不敢動,耳朵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我怕老師和同學發現我那像海浪一樣吵鬧的呼吸聲。
我覺得他好聰明,知道身體可以是拿來把弄在掌中的玩具,知道哪裡有祕密通道,手伸進去,就能把我的靈魂像衛生紙一樣抽走。
他一定是和我鬧著玩,我抬頭,教室白熾的燈管閃爍一下,發出啪啪的聲音,我的身體隨之震顫,我是槍膛,子彈挾著火光通過,明暗之間,我似乎看見爸媽的笑臉。
我和女孩後來真的一起看了很多部電影,從一開始的尷尬少話,漸漸能跟上彼此話語的速度,再細部微調頻率校準,終於變成摯友。
一起坐在電影院裡,如果能專心看電影,時間就過得很快。她習慣湊到我耳邊說話,嘴脣掠過耳垂,輕如羽絨,像一隻正要起飛的雛鳥。氣音嘶啞,反覆推送,似在邀請我進到她喉嚨深處,撥開懸雍垂,觀看她聲帶的振動。
是不是有人在看我們?遠座傳出的短聲,是不是在抱怨我們?劇情與我的擔憂交疊,她的肘關節和我的碰在一起,有時直接壓在上面,我手腳冰冷,體溫像被她伸縮吸管一般的手臂抽盡。
我開始一直去上廁所,劇情無法暫停,卻可以使她暫停。
我在家裡習慣坐著小號,乾淨,又能久坐,向前俯身就什麼都看不見。我不喜歡在外面上廁所,只要旁邊有人,他們任何輕微的頭頸偏側可能都是為了偷覷,我將整個身體壓進便斗,看不見自己的手。褲子和衣襬貼著乳黃陶瓷的邊緣,我覺得自己很髒,別人和我的尿液黏附在我無法嗅聞的位置。
我總幻想在我結束的前一秒,冷顫的迷茫中,小便斗裡,或是馬桶底部,不懷好意的手指伸出來,揪住我,扯開我的褲頭,彈指的勁道讓我疼痛,不知從何處傳來戲謔的低語:「小嘰嘰。」
當我還是幼童,剛被媽媽褪下尿布,晾著解脫的涼意,調皮跑開,立刻被長輩拉進他們喝酒的圓桌邊,彈小嘰嘰,「好可愛喔。」剛剛爸爸教我一一親暱問候過的大人,和爸爸媽媽一起圍著我笑,我看見他們頭上盤繞著群飛的蚊子,幾隻肥大的像子彈那樣朝我光裸的下體飛來,加上尖銳的笑聲,讓我身體感到強烈的刺痛。
紅色的大圓桌,包住圓桌的粉紅塑膠紙沙沙翻攪,我腳無法碰觸的地上布滿溼軟的煙蒂和煙灰碎屑,我按著褲襠,不可以讓別人看見,好討厭的感覺,甚至討厭自己。藍色的光,遠方似乎有海的聲音,我想起一部電影,《月光下的藍色男孩》,不記得是和女孩看的,還是自己去看的。
細節忘光了,只記得黑人男孩滿臉是血,倒在其他青少年兇狠起落的腳下。以及藍色月光下的瘦弱少年說著:「你是唯一一個碰過我的男孩」。這部電影後來在線上影音串流平台可以看到,點開app時的音效巨大地像兩記鳴槍。
我偶爾一個人去看電影,覺得孤獨的時間添加了不少情調,進電影院時是白天,好像把太陽一起拖進黑暗的影廳,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周遭瀰漫著高雅的慵懶。
二輪戲院無需劃位,也不會滿座,通常不會有人坐在旁邊。有次影片播到一半,身邊的椅子搖動,老舊機括摩擦的聲音,椅墊坐實後,重重噴氣聲響,溢出墊內深處陳年的汗酸味。一個中年人出現在我身邊,他的呼吸聲像暗夜中的海濤,手故作不小心地落在我的大腿上,手汗滲出,熱又黏。
他可能也是一個人來看,想有人陪伴,想要有朋友坐在一起。我聽見長輩的笑聲,可能是他的,或是電影裡的聲音。
我一直看著電影螢幕,覺得電影的故事好真實,現實反而虛幻,過去出錯的記憶,將反覆錯剪到現在。我想扭頭旋身跳進那片白色的布幕,讓光影淹沒我,總是電影畫面才能順暢地翻轉,一幕一幕轉場切換如水花噴濺。
為什麼不離開呢?我也多次問過自己。念頭被掩蓋在某種模糊的感覺底下,無法穿透,我被切割成不同層次,有些身體脫離了意識。
我想起有些動物或昆蟲會那樣假裝死掉,徹底凍結,我的身體往座椅另一端靠,擠到扶手下,仍無法縮成一顆球。一切仍在繼續,那雙手是不是已經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了?聲音和畫面漸漸包在壓克力材質的球體外圍,我向核心收縮變小。我低頭看,黑暗中隱約看見座椅上有一灘黑漬,冒出好多人的手,大人的、小孩的,在兩胯之間像斷頭的蛇一樣翻騰,這些畫面好真實,只有那雙手是可棄的誤證。
之後跟別人說,沒人會相信,是我自己的問題,證言將被竄改,我是一個有罪的人。一雙中年男人的手,完全掌控我情慾的開關,我和他一起喘息,在電影院的白幕上疊印出猥瑣的影跡。
電影播完後,只剩我坐在位置上。我明確記得電影的所有劇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整串響亮的槍聲,那把槍黑得發亮,從畫面都能感覺到握起來的重量,槍響時我的身體跟著震動,明明說電影是真實的謊言,有時竟能取代真實。
我和女孩一起看過二十部愛情電影之後,在她二十歲的那天,正式在一起了,她說這是她刻意安排的,超級精密而艱難,絕對無法暫停的任務。
再看過幾部電影,可能是檔期的問題,愛情的題材少了,大多是驚悚懸疑、動作冒險、軍事戰爭類型。一次接近深夜,走出電影院,我們沒說話,我正專注練習趁著記憶猶新把劇情記下來,機車格其他車都散開了,回頭發現,她落在離我很遠的地方,等她接過安全帽的時候,她問:「你心裡還掛念著誰嗎?你是不是愛著誰?忘不了她?為什麼你心思好像都不在這裡?我怎麼做,向你靠近,卻永遠隔著一道厚牆。」
我正狐疑,她說話怎麼好像台詞。她突然吻上我,初臨的吻,舌頭鑽探過來,碰到我的牙齒,她頓了一下,挪開嘴脣,問我:「是我讓你不舒服嗎?」潮氣噴在我臉上,我困惑搖頭,在口腔裡啜吸牙齒,怕她沾染什麼怪味。她接著說:「你的身體比你誠實,你一直退後,你完全不享受。」
我指著我們身後偶有車輛來往的巷道,「這裡太多人了,我會緊張。」
我發動機車,她沉默地坐上後座,猶豫了一下,手才勾抱上來,我又輕輕震了一下。
她語氣焦躁地問:「這樣也不行?」
我解釋:「我說過了,我怕我腰上肉太多,有點丟臉。」
她捏了捏,「還好啦,你想太多了。」
她把我捏得很小,我真的以為我是一個想太多的人,身體也微不足道,即使我覺得這根本不像是我的身體,連我自己也不熟悉它的反應。不如說,我更像是和她一起碰觸試探,和她一起為我不尋常的反應而訝異。
我的身體訊號速率很慢,無法同步,當她已經點擊下一步,我還是旋轉符號,正在讀取歷史頁面。她每一個動作都特別巨大,我要花更多的氣力與時間,做出大幅度的動作,才能跟上。
國中的時候,一個女同學約我去圖書室讀書,讀一陣子到樓梯間休息,她將我攬進懷中,她有比其他女孩更豐滿的上圍,為了要讓我們的身體靠得更近,我的胸朝內擠壓,隨時要向後彈開,她比我高,伸長脖子找到我的臉,熱氣噴在我的額頭和眼睛,我擦過她的肩頸,把頭扭到另一邊,嘴角都是我拖擠出來的唾液與涔涔下流的汗水。
回到長桌,我複習剛才背下的重點,但一點也想不起來。她的大腿貼著我的,即使冷氣低溫,我身上滲出一層又一層的溼氣,眼鏡冒出水霧,書本上的字高高低低地浮蕩,所有的記憶都被裹進水滴裡。
圖書室安靜無人聲,唯一嘈雜的是站立型的空調,像個活人一樣抽噎與發嗝,彷彿連空氣都跟著晃動。唯一的出入大門,快關上時總會被油壓式門弓扯過頭,門軸發出巨大的撞擊聲。
我總會中槍一般地回頭窺望,想著何時應該離開,她趁機會湊近臉,四片嘴脣輕輕摩擦,她無聲地笑著,把手壓在我的大腿上,越來越往內側滑動。
我死盯著書本,焦距模糊,我瞬間縮小了,長久的時光也被揉成一瞬,我像一顆冰塊,滑入所有人冒著熱氣的手中。
最後一次和二十歲女孩看電影,是當時宇宙正在成形的超級英雄電影,可能是《鋼鐵人》。我逃避黑暗中從各處冒出的碰觸,為了讓她暫停,又去上廁所了,走出廁所後,再也受不了身體不知何處的黏膩感,按下電梯離開電影院,電梯們打開前,背後傳來悶沉沉的一聲「碰」,影廳裡猛烈的槍聲。
我忘不了那些槍聲,我歉疚地想這會不會變成她的槍聲,她會牢牢記得這部我中途缺席的電影劇情,還是跟我一樣,再也想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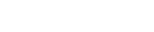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