蹓躂古巴
中國時報【敦誠】 泰勒教授說,古巴人如同所有人,不會很快跟觀光客推心置腹,還不熟悉之前,古巴人同樣經常信口開河。我到古巴的東方城市聖地牙哥時,另以「驚悚」的方式,體會到了泰勒的經驗。 龍蝦 泰勒(Taylor, H. L.)是美國紐約大學都市規劃教授,以六年多光陰,研究古巴首都哈瓦那舊城區的居民生活。事有湊巧,就在針對398位居民的訪談竣工,團隊彙整了資料,自得其樂而辦理小小慶祝餐會當天,新聞傳來,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住院開刀了。 對於2006年7月31日的古巴人,這是晴天霹靂。電視主播話語還沒有結束,餐會所有人靜默無聲,還有位年輕人飲泣,大家試圖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 卡斯楚開刀,退出古巴政經決策圈,很快過了9年,古巴還是古巴,龍蝦對古巴人的隱喻,還是沒有改變。 泰勒教授說,古巴人如同所有人,不會很快跟觀光客推心置腹,還不熟悉之前,古巴人同樣經常信口開河。這就使得外國人可能從其言行,搞錯了真相。比如,「我們古巴人永遠都沒有足夠的東西吃……」這樣的話。海外旅客對於這個聲稱,可能大惑不解。走在城鎮與鄉村,滿眼古巴多壯漢,以及虛胖的人,瘦弱之徒卻是罕見。若是真有營養不良,可能是古巴的牛與馬,乃至於麻雀,比起台灣的同類,確實是小了一號。 因此,古巴人戲稱自己沒得吃,真意是說,「我們古巴人沒有龍蝦吃!」至於海外旅客平日也很少吃龍蝦,那是另一回事,古巴人固然知道,但他們堅持以龍蝦表達自己口腹之慾的不滿足。 我到古巴的東方城市聖地牙哥時,另以「驚悚」的方式,體會到了泰勒的經驗。原先,住在尼加拉瓜的網路刊物《哈瓦那時報》主編,安排我在聖地牙哥訪問其作者,剛好是女性。由於彼此素不相識,當我在火星廣場見有人貼身,親熱地以常見禮儀招呼時,我就以為是作者了,畢竟,萬人鑽動,東方臉孔就只一人,很好辨認。 兩人沿街行,找定餐飲店,寒暄後準備訪談。「來個龍蝦大餐!」當女士喚來侍者,喜孜孜地脫口而出時,她露出馬腳了。女兒在電話中幫我約定時,她確定是說,餐後訪談,怎麼會有龍蝦大餐! 「龍蝦」當頭棒喝在先,我恍然大悟在後。對方顯然是釣凱子大亨的人,真正的作者還在「火星廣場」!已經送出的訪談禮品已經無法收回,我很快起身,掉頭離去(其實是落荒而逃),只聽到同樣錯愕的小姐,尖聲對著向廚房走去的侍者,呼喊「刀下留龍蝦,洛玻斯特(lobster)不要了……。」 評論員 拋棄了「龍蝦」的呼聲,快步回到「火星廣場」,《哈瓦那時報》作者DA消失了。返家後趕緊再聯繫,得知她的手機不是每天使用。聖地牙哥「東方」大學另有一朋友YH,與她共享,兩人隔日輪替。至今年初,古巴約有五分之一的人持有手機。 DA讀歷史出身,從事16年戲劇表演,從燈光舞台的設計到親自上陣,經驗豐富。劇團團長因癌症去世後,她先到藝術學校教了兩年書,2009年《哈瓦那時報》創刊後不久,她開始不定期評論,題材多種,至今撰述了四、五百篇。 近來,她逐漸轉移陣地,目前主要為網址在歐洲,以西班牙文發表的《古巴日報》撰述。很多人說她不該「見異思遷」,但DA自有主見,窺其原因,部分可能與語言及報酬,會有些相關。DA不以英文寫作,因此在《哈》發表的文章,另得勞動該刊翻譯,為此,是否使得稿酬少些,不得而知。但DA說,現在她為《古》撰述,兩篇所得就超過YH的月薪,而通曉英文的YH作為化學專家,「若在西方,收入會很豐厚哩。」 薪資低是古巴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DA說海外有不少人對古巴的想法很浪漫,主要是不真正理解古巴。她的意思是說,在美國與歐洲,半世紀以來的第一代至第三代移民有兩百萬,這是古巴國內人口的兩成左右。何以這麼多人往外跑?太多人對境內的生活水平,太不滿了,能走,那就決不留戀。DA說,甚至有移民西班牙的古巴人,聲稱西班牙是祖國! 西班牙是古巴的祖國?這就如同印度人說英國是祖國,或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與紐西蘭人說,英國是祖國一樣的奇怪。不但奇怪,很多古巴人勢必難以接受這種心態。1886年起,古巴人決裂西班牙人,歷經三次戰爭,最終才在美國與西班牙戰爭後,取得獨立國格。現在移民海外的古巴人,真對現在的政權有這麼大的怨懟,致使不念前賢先輩的奮鬥與犧牲所取得的獨立地位嗎?憤恨不滿之心,完全泯滅了平心靜氣之後的歷史認同嗎?DA提及的人,若有,應該是少數中的少數。 已經四十多歲的DA有兄長非法進入後,目前住在美國。她則去年受邀去對岸,若是留美不歸,依照美利堅的政策,並無不法。只是,如同所有古巴人,DA的房舍、教育、工作與醫療需要,雖有缺點卻已大致由古巴政府解決。若是因為古巴消費不足而去美利堅,健保與住房,誰來買單?若她真在去年移民美國,我在聖地牙哥的「龍蝦奇遇」,也就無緣體驗了。 人權外交官 通過《1959革命後的古巴:批判與評估》,我得知《哈瓦那時報》這份網路刊物的存在,訂閱之後,某日讀到了坎伯斯(Campos, Pedro)先生的評論,眼神一亮,有兩個原因。 首先,文末他列出自己的電郵。其他的所有評論者,幾乎無人提供聯絡電郵。在古巴,政府機關(含國營事業)與教育單位之外,上網至今不便與昂貴,但坎伯斯顯然常用電郵。電腦一開,就是工作,通訊就是一種組織活動,坎伯斯不但論政,並且同時公開電郵,宣告異端組織的存在。對古巴政府來說,這多少有點挑釁。 再者,文章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標題赫然是「古巴有兩個共產黨」。一個是新史達林官僚共產黨,一個是遍佈基層與共青團,努力提出新方式新手段,要來完成生產與服務,要求「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社會化」的共產黨。1991年,因蘇聯在1989年斷絕與古巴30多年的密切經貿往來,古共第四屆大會開始提出這類聲音與作為。到了2011年,古共第六屆大會,這個路線更見清晰。該篇文章又說,前蘇聯之崩潰,不是因為與西方交鋒,是敗於蘇共內部的新史達林主義派的既得利益力量! 坎伯斯從1970年起擔任外交官,最後一個公職是以古巴人權委員會委員身分,駐在瑞士,1993年被迫退休。不過,他所代表的立場與聲音在各種外電報導,絕少看到。 從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世界日報,到英國的BBC與衛報,讀到有關古巴政治異端的新聞時,最凸顯的是,有家人遭致官方監禁的「白衣女士」團體,或者,是經營「Y世代」部落客出名,三年前法新社曾經預測可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桑琪絲(Sanchez, Yoani);雖然研究古巴已有50多年的藍道(Landau, Saul)認為,她的評論多是捕風捉影。去年,桑琪絲與12位記者,另創辦了號稱古巴境內的第一家獨立媒體14ymedio,意思是2014年在哈瓦那某大樓的第十四樓。 這次,我們前往哈瓦那,沒有聯絡桑琪絲,但拜會了坎伯斯。當天,他等待遷居,無法外出,我們於是登堂入室。原來,目前這個九坪大小的套房月租100美元,是他退休金的8倍,太貴了,他得搬家。古巴在2010與2013年修法,將古巴人行有多年的換屋,放寬至可以合法買賣,坎伯斯得以藉此賣房,也把任職外交官所獲的車子賣了,可能也有在厄瓜多爾工作的兒女之匯款,這才使得這位體態壯實、七十開外,多次被當局「騷擾」的老共產黨人,形同有了物質基礎,得以不斷從事反黨,同時又護黨的工作。 晤談之際,一位前社會學教授,目前從事房屋仲介的伙伴來了。他準時交稿,不是電郵寄送,是以隨身碟供稿,坎伯斯的兩台電腦都開著,他正在編輯創辦已有三或五年多,已經是第161期的電子期刊SPD,翻譯為中文,就是《社會主義、參與及民主》。 我明知,但還是故問了坎伯斯,「您不會同意桑琪絲的主張罷?」西方媒體青睞桑琪絲等人,而不是坎伯斯,道理何在?好像不太有人探討,但我猜答案不難確認,應該是桑琪絲的批評所預設的古巴前進路徑,是西方主要媒體更熟悉的體制。 相比之下,坎伯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對記者來說,實在流於高調,或者烏托邦。另外,也可能是一種情緒或傲慢心態的潛意識在作祟:西方都做不來了,古巴哪裡有可能做得來。有些時候,新聞報導是一種儀式,修辭也許不同,但內涵相近或相同,是一種同義反覆,並在此過程,再次肯定「現實」;儀式如果逸軌,就不是儀式,就會招致迷惑不解。兩個古巴共產黨的說法難以見諸天日,關鍵應該在此罷。 學運領袖的忠告 七十多歲的海登(Hayden, Tom)擔任美國加州州議員18年,至本世紀第一年引退。更早,他從1960年代初,就是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獻身民權與環保運動至今。他與同世代的人相同,重要的政治啟蒙泉源之一來自「古巴革命」。 海登觀察與分析美國的動向,2013年初開始回顧與撰述半世紀的古美關係,並預言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時,美國與古巴關係將會解凍,邁向正常化的軌道。當時,訕笑的人多如過江之鯽。 但他的分析成真,去年底,古美兩國元首同步舉行記者會,宣布啟動建交工作。年初,海登出版了迷人的回憶錄,從個人的經歷、思考、評價與期望,寫了半世紀以來,兩國交往的重要事件,書名取作《聽好了,美國佬!古巴很重要》,用以致敬美國早逝的重要社會學家米爾士(Mills, C. Wright),並示傳承。米爾士在1960年8月訪談並與古巴知識份子、官員、記者與教授討論,包括與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閉門大談特談三回合,每次都是連續十八小時,出版了當時風行美國的暢銷書,《聽好了,美國佬!古巴在革命》。 海登的回憶錄有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之長,事件的選擇精確,沒有流水帳的索然無味。這是對重要歷史趨向的檢討與定位,言必有據、不託空言,公正的立論伴隨多種觀點的紀錄而出場;時代的軌跡與意義寓居在個人的傳記,遂能具體,人物活靈活現,在舞台生動演出。 卡斯楚在1959年起義成功,推翻美國扶植的巴帝斯塔(Batista, Fulgencio)政權時,他不是共產黨人。事實上,當時的古巴共產黨遵從蘇聯的「和平共存」政策,與巴斯帝塔合作。 新的古巴共產黨一直拖到1965年才告重新組成,主要由三股組織力量構成。從事叢林游擊作戰,卡斯楚為主的「七二六」運動及其成員作為主導,加上在都會區集結而祕密從事反獨裁活動的學生組織,以及舊的共產黨。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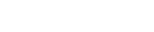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