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幻聽/左海伯
左海伯
進入八月。太陽的熱力,不減反增;火辣辣刺眼的太陽,把北京這座對流不暢的大古窯,天天都往透裏燒。
下午,我騎著自行車趕到外文局的大院時,嚇了一跳。才兩三個小時,單位已經新舊兩重天了。
一進大門,院內鑼鼓和呐喊形成的激越聲浪,像大水漫湧到我的身上;我用了很大的力,仍是抵擋不住的感覺。一時竟有些暈眩。機關大院像被誰潑了骯髒的紅漆,大字報和標語糊滿所有牆壁和報欄;那些自稱革命造反派的小青年,每人都佩戴了不知從哪兒弄到的紅袖章,個個像剛注射了雞血似地,渾身充滿了戰鬥的激情。他們把雜誌社辦公室的一二把手,反綁著雙臂,在機關大院,沸反盈天地遊鬥。
不敢正視他們。我縮著身子,順著牆沿向辦公室溜去。
我渾身打著戰,幾乎打不開樓上辦公室的門;喝桌上的剩水壓驚時,杯裏的水竟流到我的前襟上。兩股一下午都是顫的,時間像是在惡夢中經過。
第二天的遊鬥,上升了一個層次。他們糾出的是外文局的二個副局級幹部;第三天,更大的官員沒有上場,我作為赫魯雪夫的孝子賢孫,隆重登場了。他們像擰著一只營養不良瘦弱不堪的病雞,把我帶到機關大院遊鬥。敲鑼打鼓,好生熱鬧。約一個小時許,又把我帶往單位大會會議室,說要集體再批鬥。大會議室裏早已塞滿了革命小將,他們為我搭建了一個兩張桌子疊在一起的高臺。好在還有四個領導陪我,其中一個就是昨天糾出的楊求是。
他們這是把運動向高潮上推波助瀾。
我們五個人面對大眾,排成一列;他們呵斥我們低頭,胳膊向後,高高舉起,形成五架噴氣飛機。批鬥開始了。他們這天首先針對的主要是我,提的問題荒謬絕倫。
——為什麼娶個外國女人?
——中國女人不好嗎?
——為什麼不入黨?
——什麼時候與赫魯雪夫集團勾搭上的?
——你女人,與赫魯雪夫是什麼關係?是不是同學關係?
…….
我的回答,時還引起台下的陣陣哄笑,會場充盈邪惡怪誕的複雜氣氛。經過兩小時許,一個老舊的體型過於龐大的噴氣飛機,支撐不住,突然滾倒在地。他引起滿堂一次最大的哄笑後,批鬥才富布結束。我是最後允許豎起腰身後才弄明白,剛才栽倒的是楊副局長,我們鄰居。他用一只手護著額頭,被人攙扶著已走下會議大門前的臺階;他身後的地面上,有殷紅的血的印跡。像有受傷的虎豹,剛從此倉惶逃過。
那天,他們不讓我回家。讓我夜裏十二點前,寫出書面交待材料。
左右辦公室裏,都有人聲。
我寫不下去。
左邊辦公室是我的幾個同事。聽聲音,就知道他們是廖紅歌、武愛國、鐘向陽、洪衛,還有一個取個男人名字的女人,叫任紅軍。我看不到他們眉飛色舞的表情,能聽出他們個個都像過節日般興奮。我聽得斷續,但最終還是聽明白了一讓我吃驚件事,那就是下午批鬥時栽倒的楊局長,回到家裏後,不吃不喝,望著窗外的天,像失去爹娘似地,慟哭。他哭著哭著,竟翻窗跳了樓;家人趕忙送醫,不到醫院,就死了。
右邊辦公室原是檔案室,平時沒有人在裏面辦公。現在也有人在裏面說話。我聽了好久,才聽清,他們是單位的造反派。約有五六人。他們邊吃鍋巴,邊密謀批鬥我的計畫與策略。他們商定,夜裏十二點如交不出材料,要打斷我的一條腿。
我嚇得不輕。拿起筆,開始了我違心地供述。一如陰雨的暗夜,陷進寬綽的沒有邊際的泥淖,我深一腳,淺一腳,放逐自己。
我是第二天上午下班才回到家裏的。
妻子己然知道我被貼大字報遭批鬥的事。她上前,默默地從背後抱住我。我自己就感知到身體的顫抖。末了,她在我耳邊說,子煊,你怕了?
我臉上流著淚,默默地點點頭。
別怕!她抬頭,從側後方望著我。
我怕。我說。
解放前,我倆在往成都的汽車上,國民軍用步槍指著你的頭,你也沒害過怕;還有那次乘船去南京,經過三峽,所有人都亂成一團,唯你鎮定。這些,你可還有記憶?
可我真的做不到不怕。這形勢太可怕了!
夫人鬆開我,忽地轉到我面前,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她像在研究一個剛剛從死裏逃生的人。
大不了一死!作為男人,要有點氣慨!夫人說。
有人挨批,不堪其辱,夜裏已經跳樓死了。我悽惶道。
誰呀?夫人驚詫不已。
我們單位的二把手,楊局長。
你說他呀!就是住後樓西單元的楊求是?
是呀。
我早上還見到他了呀!難道他是顯魂不成;也沒見辦喪事呀。她說著,跑後陽臺上瞭了一眼。
你神經了吧,哪有你說的情況。
我昨夜親自聽見他們說的,活真活現。
你去看看,去看看。她白我一眼,做飯去了。
我看了樓間空地,切實沒有做喪事的跡象。我回憶我夜裏在單位的所聞,頭上很快炸出了冷汗。
一陣陣感覺到冷。我像患上無可救藥的傷寒。
我扯了扯我的兩只耳朵。我不相信它們對我的背叛。
我走到臥室,將耳貼到與鄰居的共牆上。沒想鄰居兩口子也在議論我。
鄰居楊子煊已被貼大字了!下午紅衛兵要把他們戴上高帽用汽車拉到長安街上游街。女聲。
多高的帽子?男聲。
最低二尺高;帽子上還用紅顏色寫上他們的名字。女聲。
這像拉出去槍葬了。男聲。
像。女聲,聽說,他那個外國女人,也跑不掉!
隔著牆,我聽得很真切。
聽到這裏,我倒吸了一口涼氣,一下癱軟在床上。全身戰得更厲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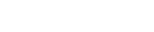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