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 打開第十九號房間
中國時報【李黎】 多麗絲,打開十九號房間的房門,讓我們看見一個女子,看見自己。To Room Nineteen,小說一開頭就說﹕「這是一個關於理智失靈了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一切的合理與智力──intelligence,不但發揮不了作用,而且眼看一個悲劇成形卻無能為力。 羅林斯夫婦的婚姻簡直是天作之合,兩個漂亮聰明匹配的人,過著平穩幸福的婚姻生活,住在寬敞的白色洋房裡,有個美麗的大花園,生了四個健康活潑的小孩(而且是再平衡也沒有的兩男兩女)……,一切都是合理的,太合理了。 可是蘇珊.羅林斯需要一間屬於她自己的房間。正如弗吉妮亞.吳爾芙寫過的那樣。她要一個自己的地方,在那裡她可以做她自己,而不是在別人的規範和要求之下的,一個理所當然的全職家庭婦女,無懈可擊的賢妻良母;一個「理智」的角色,別無其他。於是她做了一件極不「理性」的事:找到一家簡陋的小旅館,租下一間房,每天下午去待上一陣,什麼也不做──就做她自己。 她那非常理性的丈夫,發現了她的詭異行蹤之後,只能從自己的邏輯思路推論斷定:妻子有了外遇。蘇珊知道丈夫永遠無法理解,多說無益,乾脆將錯就錯承認正是有了外遇,甚至編造一個子虛烏有的情人的名字。 但她實在沒有精力再去扮演這樣一個更可笑的角色。次日回到十九號房間,享受最後寧靜的四個小時,她和她自己,然後躺到床上,在煤氣細細的嘶嘶聲中,漂向一條黑暗的河流……。 當我讀到邁可·康寧漢那本向弗吉妮亞.吳爾芙致敬的小說《時時刻刻》(The Hours),立刻想到《十九號房間》。在《時時刻刻》裡,一個洛杉磯的年輕家庭婦女蘿拉,在「賢妻良母」的平靜外表下,內心卻有著洶湧的激流,窗明几淨的家對她有如枷鎖,她想逃,她迫切需要一個完完全全屬於自己的地方,在那裡她可以讀完吳爾芙的小說《戴洛維夫人》、作夢、做任何事--或者什麼也不做。這一天,她把兒子托給鄰居,開車進城找到一家旅店,鎖上房門,感受完全的自由,她甚至想到可以就此死去──然而她現在還做不到。兩小時後她回去接兒子,煮晚餐為丈夫慶生,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然而她的兒子,那小人兒,竟然敏銳感知到他與母親幾乎剛經歷過一場生離死別。 當蘿拉走進旅店房間,終於有了她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不就正是蘇珊.羅林斯所渴望的嗎--同樣也是一個女子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而租下一間旅舍的故事。那份對自由的渴求與絕望時的慘烈簡直是驚心動魄。 我無從知道,世間曾有多少女子切切的渴望那樣一間房,卻終其一生未能得到;又有多少是讀了《十九號房間》而動心起念去尋找一間完全屬於自己的房間的……但我知道,許多年前,我也曾經是一個渴望那樣一間房的女子。有一天我終於付諸行動,在鎮上的一棟商業樓宇裡,用非常廉宜的租金租了一間地下小室。一星期有那麼一兩天,在做完家事、丈夫孩子回家之前,我去到那裡消磨兩三個小時,讀書寫字畫畫冥想甚至睡覺或者什麼也不做。一年多之後,我找到心裡的那個房間,知道自己不再需要待在一間沒有窗、看不見藍天的地下室了。 然而每當想到《十九號房間》,心中還是會感到微微的悸動。蘇珊隨著那條黑暗的河流漂流而去,吳爾芙也是讓一條河淹沒帶走了她;而站在岸上的我們是倖存者……。感謝多麗絲。 多麗絲,不疲倦不老去的書寫者。八十八歲那年,有一天買完菜回家下了計程車,發現大批媒體守候在門口,告知她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好似聽見一則稀鬆平常的新聞,無動於衷的付車錢、拿東西、進家門。記者問她有何感想?她的反應是﹕「都講了三十年了,沒什麼好激動的。」 記者們要求她多少說點什麼,她反問:你告訴我該講什麼?最後在逼問下帶些無奈又不耐煩地說:「我已經得過歐洲所有的獎了。再多一項,就是……(把手一揮),同花大順啦!」 一點也沒有「贏家」的狂喜。她早已有了她自己的房間。 (多麗絲.萊辛,享壽九十四歲,出生當時,伊朗還叫作波斯,父母都是英國人。兩次結婚又離婚,從三十歲那年二度離婚之後就沒有再婚。「萊辛」是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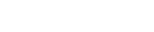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