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雪と新櫻の絆

第二人生的旅路,點水蜻蜓款款走,總有一朵花香,一道暖陽,值得被珍惜。
從台北遷徙桃園多年,歲月在不言不語不回頭中闃然泯沒,怎麼思緒未及反應,在擁有千百口埤塘,已故導演齊柏林生前形容:「宛如散落一地的水晶,閃閃發光」的國門之都,日子過得如何?時光便揚揚自若的離去無蹤,險些驚惶到不知怎麼坦坦應對。
過去,新竹石坊里是我年少成長的家鄉,尖石那羅部落是少年心靈依託的仙鄉,台北是青壯奮進事業的城鄉;而今,桃園是後中年賦閒無爭的家園;兩腳共伴並行過的地方,後來都成為故鄉。
想來,能讓我在桃園安居的理由,竟是清幽的青蔥綠樹和寬闊公園,以及我對在地人文尚未熟稔的灰溜溜之際,出現的幾位藝文友人,彼此關懷相伴,多少消弭了對陌生環境的矛盾衝擊,這一群具有過人才氣的文學人,相互涵濡,是我用時間慢慢維繫起來的情誼,後來都成為寫作歷程,閃耀靈動意象,盡入心底的意外奇緣。
如果少了交情,少了互動,無論遷徙到任何地方,終將發現,人到底為何而活?如同此刻,把對於某些人、某些事的稱心介意融入尚有幾分韻味的記憶,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也無須假惺惺的強顏歡笑;年逾古稀,面對現實,要懂從容自在,且能在已知的情況裡,看見內心世界的智慧,那便是:我決定跟著心走,在台北跌跤、受傷,就使勁放膽爬到他方,盡心竭力站起身來。
人有無患病,在於心有沒有病。從前,我是個寫作者、出版人,讀者對作品的評價差強人意,過去或更早以前,寫過不少探究生命價值與社會觀察的報導,我相信,明明確信已能領悟不少內涵,但領悟有何意義?想要持續書寫的念頭,無休止的增添我堅持的任性;於此,寫作讓我往本願更接近一些。
19世紀建築家安東尼高第說:「世上沒有新的創造,擁有的只是發現。」生命本質是一個人活,難免要承受適應新鄉人生地不熟的不安定因素,並藉時間排解,步步釋懷;時常不安也不是辦法,身邊若有幾位熟人,心情或能多些生動;純然奇特,我確實在對的時機邂逅不少值得交往的人,喜歡或被喜歡從來都不會從天而降,是內心的給予,這該是緣由於與同為文學人和睦相處的玄奧吧!
隱逸里巷數年,做了些雜役,發表數十文學篇章,出版21本書,旅日十數回,光陰未曾虛度;2022年盛夏,還讓尖石鄉公所在原民文化館,舉辦一場為期一個月的「陳銘磻文學展」,翌年春末,又在全台最美的桃園圖書館新總館舉行為期兩個月,盛大的「陳銘磻日本文學行旅私房收藏展」。天地庇佑,里居無恙,諸凡順遂。
遷居桃園是始料未及的事,蒼天垂憐,讓我意識到,後中年搬離台北羅斯福路舊居,或可招來好運,這好運即是意志裡還持有足夠的毅力和勇氣繼續創作,我用這個運氣拯救頹唐多時的自己。上蒼明示,好的事情要小聲說,不必張揚,否則決絕收回,馳驟不見。
無論夜怎麼黑,黎明總會到來,即或晴空倏忽陰沉,也比闇夜來得明亮。就在期盼能風雅老去的同時,概以大器心情撰寫和悅可讀的新書冊,這是寫作生涯最為勤懇的一次,相對身處氣派宏偉,與大自然如此貼近的起居空間,或能獲致更具清明意象的豐沛能量;可以說,我的第二人生時光,竟成可以明確回顧過往的清閒所在,要說身體狀況未盡理想也沒關係,即使住所鄰近的交通對我外出行動委實不便,時間久了,這些都已逐漸消退成無關緊要了。
活到這樣的歲數,悲情故事聽得不少,然,誰要一直活在憂傷中?如今的我,只想用和煦心情書寫一些讀起來興致方盛的人和事,如同心有困惑,不得其解,聽一聽和緩的流水聲,感覺自己正和水一起流淌著,不自覺中,原來難以理解的事,好似全覺悟了。
生命承受疫情排山倒海侵襲的這些年,無有想做的事,也不願再多說話,完全不想回憶三年來的防疫隔離有多煎熬,不去談論病毒入侵的苦難也算一種溫柔吧,那種猝然成為社會現實的議題,寫了,說了,強迫別人聽,總是惹人厭。生命何嘗不是這樣,人的今生之旅,能有多久就多久,我在這裡,許多人還在這裡,大都抱持人生就是和未來在戰鬥的啊。
很多心底的話害怕說了,人還是會離開;匆匆活過後中年,仿若已近枯竭的五衰歲月,依然不解混沌生命到底怎麼回事。敬畏人生的勵志哲理流傳萬千則,無非生老病死加苦痛。如今,白天忙碌中被遺忘的回憶,總是再次忽忽襲來。那個屬於曾經追逐寧謐和風與燦爛陽光的日子,以及和煦海風,竟能吹散喉嚨的哽咽。歲月走了,剩下的鳥叫蟲鳴,使我摸不透這一趟唯一的人生,到底有多少感想。
後來,我還是在最終的一剎意識,選擇把這些年的生存態度,後中年的第二人生,敘寫下來,讓值得歡喜的記憶存留此生:從生命樹看桃園總圖的美姿新貌;走訪桃園神社,追憶日本大津石山寺紫式部寫字間的旅情;感念中原大學向鴻全教授的晴天之氣,安頓惶惶不安的移居情緒;從櫻花滿枝椏歎賞春天市街,燦爛的花景色;在楊梅富岡鐵道藝術節,搭乘昭和年間建造的古董火車,回望與年輕時代就學大阪的父親,結伴日本鐵道之旅的印記;華麗走過林文義愛過的80年代的豐饒文風,旁及錦簇豐盛的文學出版風華;細看英氣勃勃,身居暢銷作家名銜的姜泰宇,如何經歷變動少年,行走蕭瑟青春;自嘲如櫻花飄瀟綻放又悄然枯萎,一段咸相傾慕的曖昧戀情;日日清晨啜飲一杯UCC咖啡,念及想望孤老後的寧謐韶光;紀錄出生昭和時代大溪郡,國寶級木藝師游禮海的木作工藝、就快遺忘的新竹記憶……。
文學創作從來不缺自在,獨漏欣賞自在的眼界,錯失用寬厚的微笑看待每一個字,每一個有涵義的段落,以及認真對待日復一日的書寫。曾經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走過的路、辛勤探尋日本文學地景的蹤影,不可能回頭重來,趁便記憶猶存,遂把深埋心底的昔時情愫、一期一會的感動、值得留住的青春物語,載記下來,期盼暮年的愁悶心情能在喜悅中活躍起來。
生活景色天天都在變化,著實捉摸不定,致使我無法長時間佇足回顧,這是實情,也是寫作素材;但生命不會只有美好那麼純粹,好事發生時要寫,不如意也要寫,每天以寫作迎接和結束這一天,不必介懷成名與否,成名未必是好事,它不會使人高人一等,不會讓人更有價值,是說,寫作的價值在哪裡?我活了七十好幾,寫了百餘本書,依然找不著有意思的答案,就是繼續寫呀,文學是看得見,聽得到的生命精靈,唯其喜歡,何足在意盛名與否,且無需追問:為什麼要寫,要不停的寫?無非想把80、90年代的生活影像牢記下來,像魔法一樣賦予生命色彩,讓那些足以再次回到腦海的記憶,幻境成真。
那是某年初春的日本遠行,為採擷文學地景寫作材料,妻女伴隨從新大阪搭乘JR特急車「東方白鸛號」,去到西北方的城崎溫泉,打算尋訪以《暗夜行路》出名的志賀直哉,在當地養病療傷的蹤跡,或是其他;車抵月台,適巧見到飄落鐵道,那一季冷冷的殘雪,垂掛在柵欄外幾株櫻樹的枯枝上,不意想起德永英明演唱的歌謠〈殘雪〉:
陪伴你等候火車,我在一旁不時注意時間
不宜時節的雪,正飄瀟落下
你傷感地喃喃說著:
這是最後一次在東京見到的雪
殘雪也明白飄落時,在擾嚷的季節之後
而今,春天來了,
你變得如此美麗,比去年更加美麗了
啊,如此詩意的文詞:「站在你離去的月台 看著飄落後隨即融化的雪。」時景時情,願我是那片殘雪,融為清流,滲入厚土,為早春的櫻樹綻開繽紛花彩。
衰邁久風塵,人終將老去,如櫻開落,寫作靈思亦有枯竭時,倘若只顧其眼前煩躁俗事,不覺世界遼闊,自是體會不出豁達況味。旅行又旅行,寫作再寫作,落筆五十餘載,辛苦寫的書若沒幾個人閱讀,誰也浪漫不起來。
這樣說來,實在無須沮喪,這種事充其量不過就是感受差了一點而已;好運向來不會只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那就不必有所遺憾,終歸生命充斥太多使人不甘心、不服氣的事,平靜也好,披心虛己就好。
某日午後,意外的,坐在台北公館茉莉二手書店長板木椅,一副沉靜老邁的望著玻璃櫥窗外,想著:是怎樣的顧念占據我此刻靜默的思緒?感情?生死?還是欲想?眼前僻巷雜亂無章的屋況未易,悄然掠過面貌大不同的多歷年代,驚覺同調的人生戲碼,還是舊樣式;老樣子不好嗎?世事飄搖,偶遇故土流景,男人也有想哭的時候,然,男人的淚水不能是放縱的,而是吞嚥的呀。
回想經常進出書店購書的青少年歲月,我亦是不折不扣,不食人間煙火的小文青,真是,真是;莫非是橫生逸趣的殘雪與新櫻,相互臣服的依存,並始終深信人生本相就是這樣?不要輸給歲月,坦然面對實為殘缺不全的這一生,就算不被時間允許活得更長更美好,也沒關係,我便依循念舊情意,隨興自悅書寫生命韶光相隨相伴的許多老樣子,憑倚賦別已然隨風而逝的依依青春,仍是未嘗厭倦的聆賞松任谷由實與飛鳥涼演唱動聽的《春よ、來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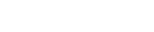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