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正義最難解一題!昔遭關押強灌汽油 心理師追蹤受難者多年、道出長輩一生之痛

「我們會預設父母照顧我們、也以為政府國家會疼惜人民,但當這個預設被打翻,是一整個世界觀的動搖,他會無法理解這事怎麼發生在我身上,我做錯什麼、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況且很多受難者都是知識份子、認真讀書的好學生,他無法理解事情會變這樣……」
儘管台灣於2017年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22年5月份促轉會提出總結報告,轉型正義看似有極大進展,卻仍有一部份的受難者被留在往日時空,面臨「政治暴力創傷」──他們可能曾被刑求強灌汽油、活在無法拯救自己的絕望、出獄後被社會排擠,儘管靠自己的力量努力生存至今、也終於迎來可以追尋真相的時代,卻依然可能在夜半時驚醒、以為仍活在監控之中、連去醫院都會想到監獄裡的日子,這些傷痕甚至還還不被台灣社會理解。
該如何真正讓這些受苦的靈魂自由,正是2021年成立之「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最關切的課題。協會由心理、社工、醫護、職能治療等不同領域工作者組成,而從心理師兼個管郝柏瑋、職能治療師N(化名)、心理師朱世宏多年陪伴受難者經驗之分享,或許也可窺見真正「社會和解」的一道希望。
台灣長輩超越半世紀之傷:跟社會格格不入的感受,比在監獄裡更像酷刑…
雖然如今台灣對於「創傷」的討論已相對開放,例如家庭暴力創傷、性侵創傷、童年陰影、精神疾病,所謂「政治暴力創傷」卻是一個相對新的觀念,光是要理解到台灣社會曾發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這樣的悲劇就有難度。

「政治暴力創傷」是個相對新的觀念,光是要理解到台灣社會曾發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這樣的悲劇就有難度(資料照,不義遺址安康接待室,顏麟宇攝)
如今投入「政治暴力創傷」工作的心理師郝柏瑋分享,最初會知道1947年「二二八事件」是在課本上看到的,「以前不太覺得會有什麼影響,就覺得這是個歷史事件。」至於白色恐怖就更晚,課本沒說、到了大學才知道,直到2014年台灣發生三一八運動、朋友們深受警察鎮壓後的陰影,郝柏瑋才更深刻去追尋國家暴力對人的影響,並在2019年開始加入學者彭仁郁發起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培訓工作坊。
職能治療師N表示,自己認識台灣歷史的過程可能跟郝柏瑋差不多,是在2014年三一八運動看到政府對學生的暴力鎮壓後覺醒、投入醫療團隊,而後也在2019年參加轉型正義談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相關的工作坊。此外,當紀錄片《蘆葦之歌》問世、談起慰安婦所受創傷,N也更深刻感受到我感受到戰爭跟政治對人造成的影響。
與促轉會合作密切的心理師朱世宏則說,自己原本是讀商學院會計系的,但在大學時讀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的心聲,也對這些台灣歷史的見證者產生不捨之情,「書裡會寫到很多被抓的經過,像基隆有軍人用鐵絲把人串起來,那時看到就非常震驚,怎麼會有這麼不人道的事情發生、用這種方式對待你……」後來朱世宏轉攻心理專業時,自然也忘不掉這些人的存在、思考受難者與家屬的心情有沒有人關照,便參與中研院關於政治暴力創傷的相關工作坊。
雖然郝柏瑋、N、朱世宏在之前的人生對「政治暴力創傷」接觸有限,由學者彭仁郁開啟的工作坊,確實給他們不小的衝擊。例如知名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曾經歷好友被誣「再叛亂」遭槍決的悲劇、經歷自己坐牢讓父親抑鬱而逝又見不到最後一面的遺憾,郝柏瑋說,雖然對蔡焜霖的第一印象是「和藹可親」、不會想到這爺爺之前遭遇了什麼,但聽爺爺分享,他就知道更多說不出口的傷、在監獄裡的處境──雖然如今蔡焜霖看來就是個慈祥的爺爺,也是在女兒偶然回家跟爸爸出遊待同個空間過夜後,女兒才知道爸爸到現在都還會做惡夢、而且爸爸不知道自己數十年來都在做惡夢。
出獄後也不是結束,例如從馬來西亞來台灣讀書、被誣指捲入「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陳欽生,郝柏瑋從工作坊知道陳欽生出獄後無法返鄉、在台灣沒有身份證、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頭的狀況,「很多面向我以前沒想過,原來酷刑不是結束就結束了,後續有各式各樣折磨人的方式,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卻因為雇主被關切、被講幾句話,工作就沒了……他們說,跟社會格格不入的感受,比在監獄裡更像酷刑。」
一代接一代的恐懼:當這些情緒無處去,最可能接收的就是你的家人伴侶…
這些台灣長輩經歷的還有對人際關係感受徹底斷裂,當年特務要求他們供出身邊的人、逼他們出賣誰、或是他們在獄中看著誰被槍決,就是極大的陰影,郝柏瑋說:「很多受難長輩會過意不去、覺得很對不起哪些難友,或覺得都是因為我才牽連到我的家人……這些事其實不該發生,但發生後,很多受難者究責的是自己。」N也說,有個前輩在服刑期間無法回家奔喪,那前輩後來也一直覺得爸爸過世都是自己的錯。
或是刑求,這也絕不只是肉體上的疼痛,郝柏瑋便說:「酷刑當下當然是痛,但更可怕的是,後續你會無法相信對自己身體的感覺,你身體的感覺不是你可以決定的、是別人可以主宰的,這會破壞很多對自己的掌控感……」同樣有心理背景的朱世宏則說,光是一個冤案「莫須有」的罪名就會讓人受到很大傷害,更不用說被關在牢裡面對的是未知,「你知道你被指控,但不知道對方接下來會做什麼。」
一個政治案件的審訊不只是問你做了什麼,也會認定你身邊一定有同謀、逼你說出認識的親友在做什麼,朱世宏說,最掙扎的就是如果案子被認定有涉及其他人、被特務逼迫出賣身邊人的過程,「不管你講或不講都一定有傷害,等於要過道德那關,你可能要終生背負著出賣誰的罪惡感。」至於疲勞審訊過程也符合心理學上的「知覺剝奪」,當一個人被關押在暗不天日的房間、沒有任何人跟你說現在被關了幾天、現在是幾點,那精神一定會渙散掉、清醒的心智徹底被弄暈,「這段歷程很多東西會印記在你的心理、生理,卻不一定被察覺到,現在政治暴力創傷很難做的,就是當事人很難認知到這部份。」

當一個人被關押在暗不天日的房間、沒有任何人跟你說現在被關了幾天、現在是幾點,那精神一定會渙散掉、清醒的心智徹底被弄暈(資料照,安康接待室偵訊工作區,顏麟宇攝)
當一個被國家誣陷關押,更恐怖的,還有更多是對國家與社會信任的崩解,郝柏瑋道出那份無助感:「我們會預設父母照顧我們、也以為政府國家會疼惜人民,但當這個預設被打翻,是一整個世界觀的動搖,他會無法理解這事怎麼發生在我身上,我做錯什麼、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況且很多受難者都是知識份子、認真讀書的好學生,他無法理解事情會變這樣……」
這不只毀掉一個人,也毀掉他身邊的人。郝柏瑋在政治暴力創傷培訓課程也有見到受難者配偶、二代,從這些家屬分享可見,受難者也可能因為創傷對家庭的掌控欲更高,例如限縮孩子發展、不讓孩子交朋友、懷疑配偶出外接觸的每個人,讓家庭活在高壓氛圍。
「長期受到暴力,一定有一些怨、不公平的感受,當這些情緒無處去,最可能接收的就是你的家人伴侶,可能會咆哮啊、罵啊打啊都有……他可能不信任外面的世界、什麼都不講,但因為對家人還是信任的、比較可以坦露,一個人被不當對待後的暴力也會呈現在家庭裡……」郝柏瑋說,受難者二代可能也會面臨人際上的痛苦,也會懷疑:我的家這樣,我的另一半可以接受嗎?我交朋友可以講多少、他們可以理解我嗎?
職能治療師N走入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見到的是,長輩可能有一些在一般人看來就是強迫症的行為,例如反覆檢查門窗、質疑外頭有人在看,這些行為就會影響年幼的子女,讓孩子意識到在家裡也是無法放鬆的、影響孩子的身心狀態,「這成長經驗佔了二代甚至三代生命中很大的一部份,但,這事情又很不容易跟其他人說……」
當孩子被父母的苦難而波及,就會陷入困惑的情緒──到底該怪父母、還是該怪政府?「你發生的事不是你願意,但你會影響到我、我的人生會被你限制」,這正是郝柏瑋走入一個白色受難者家庭看見的心情,即便受難者子女童年充滿痛苦,「他心中一直期待爸爸跟他道歉,但他不會講出來,就連現在他也沒看到道歉的可能,也會想:道歉了,我就可以原諒嗎?」
逾4萬名受難者與家屬名單、僅660人願意接受促轉會電話訪談 「重建社會信任」依然是關鍵課題
早在1990年代政治案件平反運動前,各種陰影就已纏繞受難者與家人數十年,即便如今白色恐怖受難者漸漸願意出來談自身遭遇,郝柏瑋看著長輩分享,也知道說出口真的很難:「你要在社會大眾面前承認這些事發生在你身上,講的時候會有各種感受湧上來,但所有人都想在公開場合維持形象,邊聽也覺得滿不捨……很多長輩都無法立刻做到全面分享,時常都是片段的、一點點兜起來成為一個故事再上去講……」
明明受害的是人民、人民卻不敢出來談,職能治療師N說,有一部份也來自歷史的污名:「白色恐怖是先把你定罪,說你是叛亂犯、匪諜,別人會覺得你有做錯事……如果他們在說出口的過程又不被理解、遭受不好的對待,那就更難說出口了。」
光是說出自己經歷的事情都很難,進一步心理治療就更難,這不只在政治暴力創傷、大部份的創傷都是如此,心理師朱世宏就說:「不只政治受難案件,如果有個年輕人車禍過世,對這家庭來說也是個禁忌……我們談一些事情總會害怕別人有負面情緒,會以為我們要先把日子過好、往前看、事情過了就過了,尤其政治受難者,把事情翻出來真的不曉得要怪誰,甚至不會讓二代知道他們發生過什麼,希望家人知道越少越好、保護他們。」
也因此,據促轉委員王增勇於2022年4月30日促轉會任務成果發表會分享,即便促轉會開啟政治暴力創傷療癒長照工作、委由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聯繫,計22,028筆受難者名單(含家屬有44,000筆)也僅完成660名受難者電話訪談,進一步僅201名受難者願意接受家訪、193名進到個案服務、27名接受密集照顧──原先專業是做精神病人社區訪視的朱世宏說,即便是一般民眾接到政府關心也會滿頭問號,想說政府想做什麼、為什麼會有我們的資料、是不是詐騙集團,曾被政府傷害的政治受難者當然也會這麼想、甚至更嚴重,一開始朱世宏去督導地方團體聯繫政治受難者時,就一再給同仁心理建設:被掛電話很正常、不要太往心裡去。
該如何讓受難者願意接受國家關心,朱世宏說,首先或許是要從歷史真相切入、所有口述歷史訪談都是療癒的開始跟契機,接著個管工作原則是要「打死不退」,要持續聯繫、但又不能過於打擾──例如一位受難者,雖然訪談時有意願讓社工拜訪,受難者子女卻不希望長輩被打擾、不想讓長輩再回想過去痛苦的事,於是工作人員們透過寫信方式聯繫。雖然最後結果是寫了信以後被孩子看到、被擋掉,只要有可能聯繫,工作人員都不能放棄。進入家庭以後,團隊也不能心理師只做心理師的、復健只做復健的,要讓跨專業不同工作者能隨時回應到長輩當下需求,也仰賴培訓出來的敏感度。

為何政治受難者仍需要政府主動關懷,就是因為他們曾受政府負面影響、政府主動關心是責無旁貸(資料照,安康接待室羈押囚房,顏麟宇攝)
總的來說,朱世宏認為「政治暴力創傷」不一定是一種「病」,但為何政治受難者仍需要政府主動關懷,就是因為他們曾受政府負面影響、政府主動關心是責無旁貸:「心理的東西看不到、我們的話語想法也碰不到的,但我們每天都在用這些……你不一定要預設他們一定有創傷,人都有韌性去面對人生的苦難,但如果我們有機會服務為創傷所苦、被創傷深深影響的這些人,這就是重建社會信任的重要性。」
「我希望這些因為政治暴力不再信任社會的人,可以在時空背景不同的今天有機會願意再次相信社會,這對轉型正義才是真正和解──和解前一定要理解,我們不可能莫名其妙和解,不是真心誠意的話不是『和解』,是『河蟹』。」朱世宏說──被埋藏數十年的傷口確實很難被撫平、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但這依然是轉型正義重要的課題,去善待那些被國家傷害的生命、實現真正的正義。
一起面對台灣傷痛歷史、走過創傷,請參考「向生馬鞍藤: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臉書粉絲專頁(連結)
更多風傳媒報導
相關報導》 八二三砲戰英雄成階下囚!蔣介石不敢說的老兵秘密:在廁所的時候,我們反而活得最像人
相關報導》 蔣經國時代「加害者」心聲首曝光!校園線民嘆體制逼人:我真的不喜歡、做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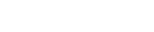 Yahoo奇摩運動
Yahoo奇摩運動 